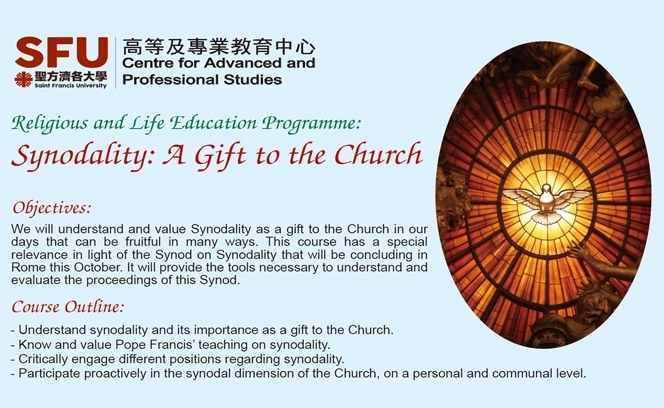悔改與身份認同
一九三三年一月三十日,納粹黨開始在德國「掌權」。而從一九九六年起,每年一月二十七日,即紅軍在一九四五年解放奧斯威辛(Auschwitz)集中營的紀念日,德國聯邦議會都會進行紀念納粹主義受害者的活動。德國人民是如何既認清國家罪行,又沒有放棄「德國人」這身份的呢?在我們今天討論自己是「香港人」還是「中國人」時,可以借鏡戰後德國有關身份認同的爭論,在「輸打贏要」和「自動認同」以外開闢另一思路。
哈巴馬斯(Juergen Habermas)曾用「斷裂」來形容戰後德國應有的國民身份認同。這斷裂並非指地域性的分割,須以統一來「修補」,或是歷史性的裂縫,與叔父輩「劃清界線」,而是文化傳統和道德層面的斷裂。「我們接受這令人不安的政治責任嗎?我們接受這由德國人所犯的、支持和容忍的文明崩潰所造成的責任,成為我們斷裂的國家身份認同的組成元素嗎?斷裂只是指這責任代表一種意志,去中斷引致國人走歪路的思維習性在自身傳統中延續。」(Die Zeit, 1999.3.31)換言之,斷裂的身份認同可以是負責任的道德抉擇,而非「輸打贏要」。我們甚至可以說,面對國家罪行和文化罪宗這一歷史以至現存事實,只有這樣的斷裂才是有承擔的國民態度。
哈巴馬斯和其同道不論在八十年代的「史家爭端」,還是九十年代關於應否在首都樹立國家罪行受害者紀念碑的爭論中,都堅持一個觀點,就是罪不止於上一代人,因為受國家傳統文化孕育的和繼承國家政體的後代,必須共同承擔在這傳統和政體中所產生的國家罪行的責任。「簡單的事實就是,後生的世代都是在那一種生活方式中長大......我們的生命與那一個生活背景——一個奧斯威辛確切是可以發生的背景——並非是偶然,而是深入地扣在一起的。我們的生活方式與我們父母和祖父母的是相連的......我們當中無人能從這歷史環境中偷走出來,因為我們的身份認同與這環境是不可分解地交織在一起的。」(Die Zeit, 1986.11.7)
既然是不可分解,那又何以「斷裂」呢?我們或可在馬丁布伯(Martin Buber)對於悔改的論述中找到理解這種戰後德國身份認同的線索。布伯指出,在良知領域內「贖罪」的人有三件事要做:明照自己的罪,堅持自己罪人的身份和獻身重建受其罪所破損的存在秩序。在堅持身份認同這一環,布伯說:「第二步是在(第一步)所獲得的謙卑認知中,堅持自己過去與現時的身份,即使在現實中這人現在的生命已昇華遠離那罪的境地。」(Buber, Schuld und Schuldgefuehle, 1958, p. 41)布伯的論述正好說明「斷裂」和「堅持」兩者的必要性:沒有斷裂,即沒有自我審視自我的距離,就沒有徹底明照深層次的罪的可能;但是沒有堅持,重建秩序的重責又由誰來負呢?
無容置疑,戰後德國的經驗與今天中港身份問題之爭存在不可比較之處。但單從國家罪行和國民身份認同的關係這層面,前者仍是有可供借鑒之處的。我們當中有的不想提起「分化認同」的國家歷史和時事(還有民調!),因為這不符合他們美滿國家身份認同的設想;我們之中有另一些不想提這些話題,認為這與他們現有的身份認同無關。但從哈巴馬斯的「斷裂」和「堅持」中,可以看到他們共有的錯誤:對國家罪責的輕率和對受害者及其家人的不顧。可以肯定的是,在我們面對六四和文革後秩序重建重責的今天,「因祖國強大而自豪的香港人」和「河水不犯井水的中國人」都不是具備悔改意識的身份認同。
在二O一O年的一次問卷調查中,有五成八的德國青年(十四至十九歲)表示不認同「納粹歷史記憶會阻礙德國人自我認知的健康發展」。(Zeit Magazin, 2010.11.4, p. 38)今天的華人青年對自我認知的健康發展又有何看法?
- 伸延閱讀:余杰,從柏林圍牆到天安門,2009。
- 作者為香港大學歐洲研究系博士候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