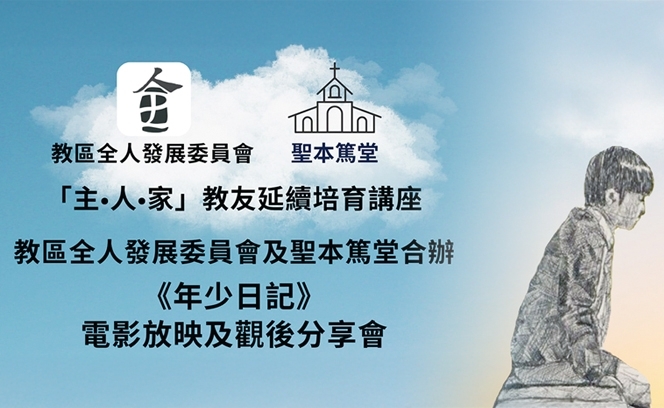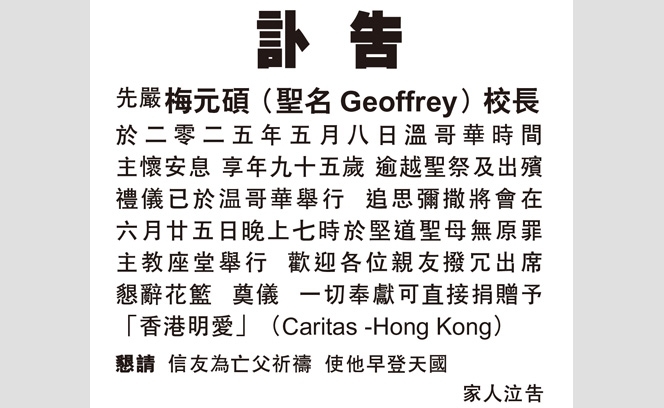【在人間】俯瞰
有位素未謀面的朋友,讀了我給小孩子們寫的書,給我留了兩行字句:
「就看見過去俯瞰著自己,
走著走著我們都不見了。」
不知這話出自何經何典,還是朋友妙手偶得,頗以為是智者之言。讀時心有戚戚,翌日醒來,夢裡滿腦旋律,盡是昔人的天鵝之歌:老巴赫由讚美詩改寫的管風琴前奏曲「來吧,仁慈的死亡,賜福的安息......」是那樣平淡。莫扎特的安魂曲也聽不到沉重與悲哀,只滲透著自足與要撒手時的泰然。貝多芬的最後兩首四重奏亦悲亦喜,卻不無幽默,令人想起李叔同圓寂時那句「悲欣交集」。貝氏愈近晚年作品便愈費解,也愈動聽,洗盡以往的偏執,多了許多不確定性和寬厚。我猜若他能多活些日子,所寫的定比獅吼般的「命運」、「英雄」和「合唱」更淳和如老酒。人到一定的日子總會回頭自省吧?蕭士達高維奇最後一首交響曲不是把自家寫過或心儀過的主題來了個諧趣改寫嗎?英雄老去亦尋常,有道世事總是在重演著自身,先以悲劇,後以喜劇。從這觀點看,所有令人嘖嘖稱道的也許都不外如是。把自家扮成小丑並非自虐,而站高了一個層次。巴爾托克臨終時喃喃自語:「真遺憾,我腦袋裡還有那麼多東西沒寫下來!」聽他還未寫完的那首第三鋼琴協奏曲,一反以往的冷峻和狂野,出奇地溫情,甚至有一大段仿如小孩在曠野裡嬉遊,洗盡鉛華便難免返樸歸真。也許上天認為他做的也夠多了,劃上句號怕為他更好。人的濟遇不同,命運也不同,難免有人走得百味紛陳。馬勒第九交響曲就充滿對死亡的不平和生的留戀。沈從文最後的話卻是「我對這世界沒甚麼好說的」,也許他身邊的人和事真令他太失望了吧?
不管帶著失望、淡然或微笑回看世道,我們誰都在俯瞰自己。所謂對世事的經驗之談,常常免不了夾帶著自家的身影和吃透的甜酸苦辣。人生的費解就在於,你苦苦上下求索,到略有所知時,離消失的日子已不遠。而又有另一批人重蹈覆轍,一代代人都像息息法斯在推著那永遠滾下的巨石,誰都只是匆匆過客。大不了只在人人走過的路上,留下些許軌跡,未必於人有益,但願別誤人子弟,如此而已。沒有人會以為已活得夠多、做得夠多,也沒有人全無憾事。人都逃不過告別,命運待每個人也未必公平。昔人告別朋友時以此緬懷:「錦繡心胸冰雪面,舊日詩名,曾道空梁燕。傾蓋未償平生願,一杯早唱陽關勸。」能如此俯瞰,即使活得最不濟,何憾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