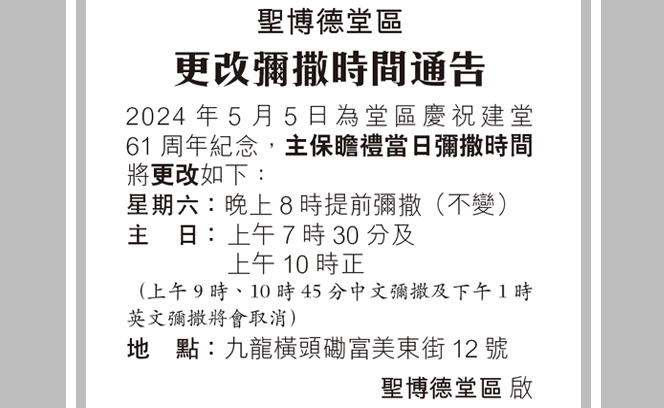從歐洲教會史探視澳門
(二)政教互動
主教區是一個地方教會的具體體現,主教是一個地方教會的領導人,他與管理普世教會的教宗保持聯繫。主教的職能及形象每每隨歷史的發展,更好說,隨政權及教權的互動而有不同。總的說來,政教二權有對立、分立、合一、合作四種狀態﹔由中世紀起到近代,大部份時間,政教二權都處於合一或合作中。當政教二權合一時,由於封建制度的關係,主教也就成了一方諸侯或地方首長,是以在一些教區主教往日的牧徽(其實牧徽是相應於歐洲封建時代爵位的徽章)上可以看見一面有一根牧杖,一面有一把長劍,象徵二權合於一身。
澳門主教區成立的時代正是「海洋大發現的時代」,教宗亞歷山大六世於一四九四年裁定Tordesillas 協約,把東西兩半球分別劃給葡萄牙及西班牙兩個天主教海權國家管理。從此以後,不論來東方經商或傳教的人士,都必須獲得葡王的認許,葡王享有「護教權」(Padroado),即葡王給予教會經濟和政治的庇護,而教會則為葡王的臣民及澳門區內外的原非臣民做開化、感化、皈化、教化等牧靈工作。這種「四化」的工作既有宗教又有政治的意義,換言之,一個領了天主教洗禮的華人等同於一個「葡化」了的華人,最初時,除了領到一個洗禮的教名外,還必須改換一個葡萄牙名字,甚至穿葡萄牙人的衣服﹔領洗紙相若於官方的出生證,直至一九八○年代,澳門人單靠一張領洗紙,就可申請領取葡國公民身份證或護照﹔而澳門主教和神父是葡政府的領薪公務員,這種情況一直維持至澳門回歸祖國為止。我推想,歷任主教未上任前會在澳督前宣誓效忠國法,就像歐洲某些有政教協約的國家的主教們一樣,如數年前柏林大主教就職前在電視上向市長舉手宣誓。
澳門昔日政教相依的遺跡,今日可見於五個社區和堂區重疊一事上:為了推廣行政效率,新澳門增設了好些社區,但有五個社區依然沿用其相對堂區的名稱和範圍,即花地瑪、安多尼、聖母望德、主教座堂及老楞佐。
正如甚麼東西都有正負兩面,護教權也不例外。它一方面給教會帶來一些好處,但另一方面它也要求教會做出一些妥協:首先,澳門主教必須是葡籍人﹔其次,教會服務的優先對象是葡國人,這就說明了一些奇怪的現象,為何直到二次世界大戰後全澳只有一個華人堂區,又為何直至今天,平日可以分享主教座堂的華人教友,一到聖週時就要退到其他聖堂去參禮,好把座堂讓給葡籍教友去使用。
澳門的政教二權從一開始就緊密合作,但也清晰分立。葡王委任的總督是澳門的最高當權者,而主教則是教會的領導人﹔後者在市議會中有一席位,是澳門的第二號人物,看他辦公的主教府的外型就與總督府一模一樣,只是比例上小了一點,注意它被稱Paco(Palace)「宮」,而非一般的Bishop’s House。澳督在參加主教座堂的隆重禮節時,是坐在主教對面特設的神職人員座位上。
護教權本是天主教教宗與各國政府行之有素的一種「政教協約」。它源自羅馬帝國,羅馬帝國的皇帝也是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他有維護及推展宗教的職責(Defensor Religionis)。當羅馬皇帝及羅馬帝國崩潰後,繼之而起的中世紀的皇帝一旦成了天主教徒,大司祭之職就轉移到教宗身上,而護教(傳教)之職則仍由皇帝來擔任。這種分庭抗禮之事已見於查理大帝,到了第十世紀以還的鄂圖(Otto)皇朝則更為顯明。
為了在易北河東部推進殖民及傳教,鄂圖大帝在易北河中游,建立馬德堡為帝國首都並大主教區,同時在它稍南的上游設立邁森(Meissen)主教區。易北河成了天然的疆界和防線,而兩個新成立的教區,就成了向東部移入的斯拉夫人推進殖民和傳教的橋頭堡。
(三)中葡關係
這個政治和傳教配合的策略,也見於澳門開埠的歷史中。須知道,葡人最初向中國政府租借的,並非今天的整個澳門,而只是半個澳門而已,即從媽閣到大炮台為止。從東望洋山起沿東望洋斜路到大炮台、再從大炮台下至內港,這一條界線就是澳門最初的城牆﹔這條界線今日已不存在,但在海事博物館的「澳門歷史模型」中可約略看見,而在大三巴牌坊的西側,仍屹立着一小段舊城牆的遺址。城牆外一大片土地是人烟稀少的農莊和村落,它們的名稱至今仍保存下來,如塔石、台山、望厦、沙梨頭等。葡人後來把租借範圍推廣至關閘,但這一區直至上世紀的四、五十年代,仍有不少空曠的地方。
(中╱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