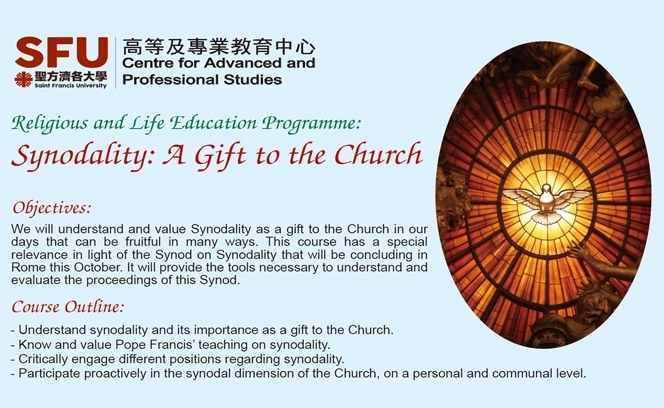保祿、佔中、拒共
十八世紀的歐洲,出現了一個工業及從商的社會,與傳統農業社會對抗。在這場激烈鬥爭中,教會站到傳統農業社會那邊。新興力量為解放困在農村內的農奴,讓他們自由進入城市,提供工業社會必須的勞動力,就必須打倒傳統農業集團和它的支柱,而其中一條重要支柱,就是當時的天主教會。
踏入二十世紀,制度鬥爭重點經已轉移。這次是發生在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和以蘇聯和中國為首的社會主義體系之間。在鬥爭最劇烈的時候,教會傾向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聯手,對抗社會主義。
由保祿開始踏足乃阿頗里至今二千年的教會經驗,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啟迪。而在香港,當我們開始面對一九九七政權轉易時,梵二已經是大約二十年前的事了。梵二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清晰表明:「教會是人類超越性的標誌及監護者」,「憑其職責和管轄範圍決不能與政府混為一談,亦不與任何政治體系糾纏在一起」(#4)。
不錯,教會關懷弱小,致力維護公義、人權,卻也超然於任何政治經濟集團的陣營之外,更不成為任何一派的鬥爭工具。對於這一點,教宗本篤十六世在致中國教會書(2007)中進一步作了澄清。他說:「教會不能、也不應該自己介入實現正義社會的政治角色中;⋯⋯正義的社會不能由教會來實現,而是由政治來實現。可是教會特別要努力地為正義而開放人的理智和意志。」(#4)
面對本地政制發展,香港天主教會公開支持民主發展,為普選發聲,可以說是秉承了這一「為正義而開放人的理智和意志」的原則。至於在「拒共」和「親共」兩條政治路線的鬥爭中,若在有意無意之間,讓人感到教會是站到某一個陣營之中,支持一方,反對另一方,就是混淆了自己的角色了。
「沒有愛,甚麼也不算」
朝聖團給我留下的最感動的記憶,是土耳其保祿出生地塔爾索和保祿曾經宣道和被猶太人迫害的依科尼雍這兩個地方的基督徒小團體。前者主要是由三位居住塔爾索(其中至少一位居住了十九年)的修女和一位教友組成;後者主要由在此服務經年的兩至三位教友志願者所組成。
在一個基督徒與回教徒經歷了幾百年戰鬥、為爭奪土地、人民與宗教控制權不惜互相殺戮的地方,這兩個團體為普世教會展示出全新的見證。他們沒有任何權勢,不能主動向外宣講福音。他們不派麫粉、不辦學、不贈醫施藥。他們有的只是他們自己,能夠給予的也只是他們出於愛的臨在,不設條件、不求結果、完全尊重的臨在。
格林多一間東正教堂門前用不同語言刻了保祿致格林多人前書十三章(1—13節)的愛德頌,完全恰當地與土耳其這兩個團體的見證相呼應,也恰當地為我們這次朝聖作了一次總結性的提醒。
對著一個相當成熟、備有各種神恩、出現黨派紛爭、甚至有弟兄對簿公堂的格林多教會,保祿提醒他們,愛統率諸德。沒有愛,做盡其他好事,到頭來甚麼也不是。「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奧秘和各種知識 ⋯⋯但若我沒有愛,我什麼也不算」(#2)。我可以「把我所有的財產全施捨了」,但是「我若沒有愛,為我毫無益處」(#3)。
先知的工作,愛德的工作,都必須以仁愛為基礎。在不能做先知,不能做愛德工作的地方,我們仍然可以實行仁愛。土耳其這兩個團體就是在受約束的政治環境中,以不求結果、不作任何判斷、完全尊重的臨在表達了這種愛。
這裡,我記起印度加爾各答的德蘭修女。她做愛德工作,不企求受眾領洗入教,只求印度教徒成為更好的印度教徒,回教徒成為更好的回教徒。她的臨在所表達的也是這種尊重的、溫柔的、不附帶任何條件、因此跨越一切疆界的愛。
記得盧神父在一次彌撒講道中說,等待是使命(Waiting is Mission)。對此,我有很深感受。等待是願意按捺或接得住自己內裡的心急,不向對方作任何催迫。等待是賦予空間。賦予空間就是愛(Space is Compassion)。
這裡,保祿對格林多信徒的說話也好像在提醒我們身處香港的天主教徒,在參與本地的先知和愛德工作時,在對待中國內地的天主教會、包括地上和地下教會時,也能給予尊重、溫柔、不批判、不附帶條件、不求結果、賦予空間的愛的臨在。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