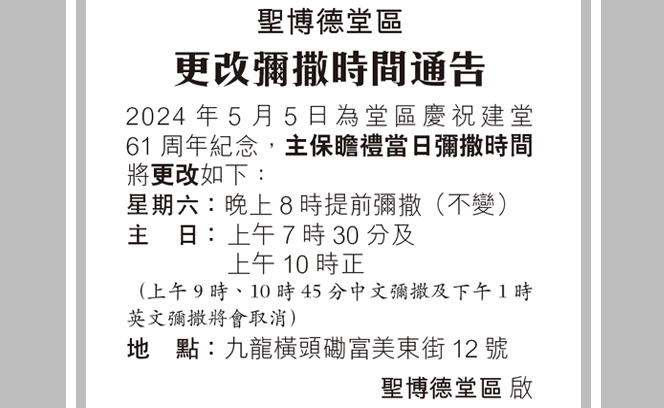【專頁】教宗接受《公教文明》訪談(一)
■ 斯帕達羅(Antonio Spadaro)
編按:教宗方濟各在今年三月上任後,以慈愛、謙卑及簡樸行動告訴世界他切望中教會的形象,就是要做「窮人的教會」。這位剛獲選為《時代》雜誌二O一三年度風雲人物、被稱許為「人民的教宗」於早前接受天主教刊物專訪時,以「上主所注視的罪人」去形容自己,訪問中更詳述耶穌會、教會及衝擊教會如同性戀及墮胎等問題。本報將於今期起以專頁刊載全篇訪問。
教宗方濟各與《公教文明》(Civiltà Cattolica)期刊 (圖) 的主編斯帕達羅神父(Antonio Spadaro)於今年八月十九、廿三和廿九日在梵蒂岡「聖瑪爾大之家」教宗的私人書房進行了三次長篇談話,斯帕達羅神父整理完畢其內容近三十頁的訪談內容後,已於九月十九日由《公教文明》期刊同耶穌會在全球其他十六份期刊同時公諸於世。教宗方濟各在訪談中概述自己的性格,說明他對耶穌會的看法,分析今日教會的角色,指出牧靈行動的當務之急,也回答關於福音宣講的問題。意原文經教會當局核准,梵蒂岡電台中文節目部十一月把訪談全文從意大利原文翻譯成中文。
聖瑪爾大之家,八月十九日星期一九點五十分
八月十九日星期一,教宗方濟各約我上午十點鐘在聖瑪爾大之家見面。我承襲了父親總是會提前赴約的傳統,先到一步。接待人員將我請到一個小廳坐下。等候時間不長,幾分鐘後我便被請入電梯。我用了兩分鐘迅速回想了耶穌會幾份期刊的主編在里斯本會議上大家同時刊登訪問教宗的提議。我同其他主編商討後,擬定了幾個大家都關心的問題。從電梯走出時,教宗已經在門前等候我。
走進教宗的房間,他請我坐在一張沙發上,他則因腰背不便,坐在一把較高的硬背椅子上。房間設備簡樸,寫字枱不大。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房間內只擺放必要的傢具和物品:書本不多、少量紙張、物件也寥寥無幾,其中有一張聖方濟各的畫像、一尊阿根廷主保盧漢(Luján)聖母像、一個十字苦像和睡眠中的聖若瑟像,很像我曾在聖米格爾大修院(Colegio Máximo di San Miguel)他當院長和省會長時的房間內看到的那尊。貝戈格里奧的靈修不是由他所稱的「調和的力量」所形成,而是人的面目:基督、聖方濟各、聖若瑟、聖母瑪利亞。
教宗微笑著迎接我,他的微笑多次傳到世界,開啟人心。我們開始談到許多事,尤其談他在巴西的行程。教宗視這趟旅行為確切的恩寵。我問他是否休息好了,他肯定的答,說他很好,說普世青年為他是個「奧秘」。他告訴我他從不習慣向許多人說話:「我能夠逐次注視每個人,同眼前的人直接接觸,卻不習慣接觸大批的群眾。」我對他說,確實如此,看得出來,而這一點偏偏打動了眾人的心。可以看到,每當教宗身處人群當中時,他的目光其實都是落在某個人身上。然後攝影機放出畫面,使所有人都能看到,就這樣教宗能夠隨意與眼前的人通過目光保持直接接觸。我覺得他滿意這樣,能夠保持自己,不必改變與人溝通的方式,即便眼前有數百萬人,就如在科帕卡巴納(Copacabana)海灘所發生的那樣。
在啟動錄音機之前,我們也談了其他事。教宗在評論我發表的一篇文章時,告訴我他喜愛的兩位當代法國思想家是亨利.德呂巴克(Henri de Lubac)和米歇爾.德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我也告訴他一些個人的事。教宗同我談到他自己,尤其是他當選教宗的事。他說,三月十三日星期三午餐當他開始意識到有被選中的「危機」時,他感覺到一股強烈和無法解釋的內心平安和慰藉降到自己身上,同時也伴隨著一片黑暗,餘下的一切都是漆黑一團。這種感覺伴隨著他直到當日晚些時候當選。
說實在的,我倒願意繼續這樣無拘束地談下去,可是我仍拿起記有幾個提問的紙張並啟動錄音機。首先,我以耶穌會士相關期刊主編的名義感謝教宗,這些期刊將同時刊載這次訪談。
今年六月十四日,教宗在接見《公教文明》期刊的耶穌會士之前,同我談了他接受訪問的重大困難。他說寧願多想想,也不願在答覆訪問的問題時那樣一氣呵成。他覺得自己時常在作了最初答覆之後才想到正確的答案。他告訴我:「當我從里約熱內盧回程中回答記者的提問時,我都不認識自己了。」的確如此,在這篇訪談中教宗曾多次中斷正在答覆的問題,好補充回答上個問題。同教宗方濟各談話實在是在活躍奔放、川流不息的思想河流中遨遊。甚至記筆記也讓我覺得因打斷這種自然的交談而感到不快。顯然,教宗方濟各更加習慣於交談而非給人講課。
喬治.馬里奧.貝戈格利奧是何人?
我的提問已經準備好,但我決定不按照預先擬定的大綱,而問了他一個唐突的問題:「喬治.馬里奧.貝戈格利奧是何人?」教宗靜靜地望著我。我問他我可否問這個問題……他點頭接受了這個提問,對我說:「我不知道哪個是最適合的描述……我是個罪人,這是個更正確的描述。這不是言談上的比喻或一種文學類型而已。我是個罪人。」
教宗繼續思索,好像沒有料到這個提問,好像被迫要繼續思考一樣。「是的,也許我能夠說我有點機靈,知道怎樣因應環境行事;但我也有點單純卻是真的。是這樣的,但最好的概括,就是出自內心和感覺最真實的那個,正是:『我是上主所注視的罪人。』」他又重複:「我是被上主所注視的一個。我經常感到,我的格言Miserando atque eligendo(因仁愛而被揀選)為我實在非常真實。」
------------------------------------------------------
我是上主所注視的罪人
------------------------------------------------------
教宗方濟各的格言取自聖貝達司鐸的講道,他在評論聖瑪竇被揀選的福音事跡時寫道:「耶穌看見一個稅吏,於是以喜愛之情注視著他,揀選了他,並對他說:『跟隨我』。」
教宗繼續說:「我認為拉丁語miserando的副動詞無法翻譯成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我喜歡用另一個不存在的副動詞misericordiando(仁愛著)將它譯出。」
教宗方濟各繼續他的反省,並轉談了我當時並不立刻理解的話題:「我不太認識羅馬,知道的事不多。我所認識的有聖母大殿,我常去那裡。」我笑了,對他說:「聖父,我們都非常瞭解這事!」教宗接著說:「是的,我認識聖母大殿、聖伯多祿大殿……可是我來羅馬總是住在斯科洛法大街(Via della Scrofa)。從那裡我常去法王聖路易堂(La Chiesa di San Luigi dei Francesi),我去那裡瞻仰卡拉瓦喬(Caravaggio)的聖瑪竇蒙召選的油畫。」我開始猜到教宗要向我說甚麼了。
「耶穌的那隻手指這樣指向瑪竇,那就是我,我感覺如他,如瑪竇一樣。」教宗此時變得堅決,似乎終於找到他尋找的形象:「打動我的是瑪竇的手勢:他抓起自己的錢,好像說:『不,不是我!不,這些錢是我的!』看,這就是我:『上主用祂的雙眼所注視的罪人。』這就是我對於是否接受當選為教宗這問題的答覆。」教宗其後用拉丁語低聲說:「我是個罪人,但我信靠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無限的仁愛和耐心,故在補贖的精神下,我接受。」
為何做耶穌會士?
我明白教宗方濟各接受當選的這句答話為他已是一張身份證,故再沒有別的補充需要。我繼續問早前準備的第一個問題:「聖父,是甚麼促使你選擇加入耶穌會?耶穌會哪方面打動你?」「我一直有更高渴望,但不知道要的是甚麼。當時我已進入修院,喜歡道明會士亦有道明會的朋友。可是我以後選擇了我更了解的耶穌會,因為那時修院由耶穌會士負責。耶穌會有三件事打動我:傳教精神、團體和紀律;這很奇怪,因我天生是個不守紀律的人。可是耶穌會的紀律、管理時間的方式深深打動了我。」
---------------------------------------------------------------------
耶穌會的三件事打動我:
傳教精神、團體和紀律
---------------------------------------------------------------------
「另外,團體生活為我而言實在重要。我常常尋找一個團體,因我並不適合做孤零零的司鐸:我需要團體生活。你從我現在住進聖瑪爾大之家這事上便能了解:閉門會議選舉教宗時我住在抽到的二零七號房間,而我們現在談話的這個二零一號房間以前是客房。我選擇住在這裡,因為當我接收教宗寓所的時候,心中清楚地感到我並『不』住在那裡。宗座大樓內的教宗寓所並不豪華,卻古樸雅緻,很有品味且寬敞,但不豪華。不過它到底似一個反轉的漏斗,裡邊寬大,入口卻太窄,只有很少人能進來。沒有人我活不了,我需要同別人一起生活。」
在教宗談傳教和團體的時候,耶穌會論《傳教的團體》的文件都浮現於我腦海中,而我在教宗的話中找到答案。
對一名耶穌會士而言,
做羅馬主教意味著甚麼?
我繼續這條脈絡,從他是首位被選為羅馬主教的耶穌會士談起,問教宗:「你如何解讀你蒙召按照依納爵的靈修,為普世教會提供的服務?為一名耶穌會士而言,被選為教宗意味著甚麼?依納爵靈修哪一點能幫助你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職責?」「分辨。」教宗方濟各答道:「分辨是聖依納爵下最大功夫的內心修行之一。為他來說,分辨是為更好地認識上主、更貼切地跟隨祂的一件戰鬥武器。我常被用來描述依納爵這一觀點的格言所打動:「Non coerceri a maximo, sed contineri a minimo divinum est」(不受最寬大的空間限制,卻能被最窄小的空間容納,這是神性)。為治理、為做長上我反覆思索了這句話:不受較寬大的空間限制,卻能在較窄小的空間內生存。這個大與小的德行就是寬宏大量,它使我們能從所在的位置觀望遠景,能懷著向天主和他人敞開的寬闊心胸做每日的小事;以遠大的視野、天主國度的視野去重視微不足道的小事。」
「這句格言為站在正確的位置上去分辨,從天主的角度體驗天主的事提供了衡量標準。在聖依納爵看來,大原則必須在地點、時間和人的具體環境中體現出來。當若望二十三世再三重複「Omnia videre, multa dissimulare, pauca corrigere」(看到一切,視而不見許多,糾正少少)這句格言時,就是以這種方式開始治理教會,因為他認為,儘管看到一切,看到最大的幅度,卻只須在少許事上,以最小的幅度上運作。可以有龐大計劃,卻藉著在少量最小的事上運作,就能實現。這正如聖保祿在《格林多前書》中所說:使用軟弱的工具,它比強健的工具更有功效。」
---------------------------------------------------------------------以遠大的視野,天主國度的視野
去重視微不足道的小事
---------------------------------------------------------------------
「分辨需要時間。許多人以為改變和革新能在短時間內實現,我卻認為真正、有效的改變總是需要時間去奠定基礎,這就是分辨的時間。有時分辨後,反而激發人立即處理最初打算以後再做的事,這樣的事近幾個月也發生在我身上。分辨過程中往往有上主的臨在──留意身邊標記;聆聽所發生的事件;瞭解人,特別是窮人。而我的選擇,包括每天與生活方面有關的選擇,如使用不起眼的汽車,都與靈修分辨有密切關聯,我的選擇符合來自事物、人和閱讀時代標記的需要。在上主內分辨亦能引導我的管治方法。」
「這解釋為甚麼我不相信突然作出的決定,我總不相信第一個決定,即當我必須作出決定時首件想到的事情;一般來說,這常是錯誤的事。我必須等待,作內心評估,以爭取必要的時間。分辨的智慧可彌補人生的模糊境地,使人找到更合適的途徑,而不是看上去似乎優越的方法。」
論耶穌會
--------------------------------------------------------------------- 耶穌會士不以自己為中心
---------------------------------------------------------------------
可見,教宗的靈修支柱是分辨,其耶穌會士身分以獨特的方式在這方面表達出來。我進而問他,耶穌會如何能為今日教會提供服務,耶穌會的特色是甚麼,以及可能冒的風險。「耶穌會是個處於張力中的團體,從根本開始已是處在張力中。耶穌會士是不以自己為中心的人,耶穌會本身的中心在修會之外:它的中心是基督和祂的教會。耶穌會若將基督和教會置於中心,它就能為自己生活在邊緣地區找到平衡的兩個基本參照點;相反,若它過於注意自己,將自己當作牢不可破、裝備完好的結構中心,就會有過於自信和自滿的危機。耶穌會必須視『Deus semper maior』(天主永遠更大)、尋求天主的光榮為最重要的事,即使我們是不中用的瓦器,也將吾主基督的真淨配教會和博得我們愛戴的基督君王放在眼前,要將整個人和全部勞苦奉獻給基督。這種張力不斷地將我們從自我提出來,令不以自己為中心的耶穌會更形強健,幫助修會更有效地履行使命,這猶如父子和兄弟情誼般的『訴心』管道。」教宗此處所指的是耶穌會會憲的一則特別會規,規定耶穌會士必須向長上「表白他的良心」,即他的內心精神世界,這樣做便於長上在派遣使命時能更有意識地予以配合。
教宗方濟各接著說:「可是談耶穌會並不容易。你若說得太明確,便有被誤解的危險。談耶穌會只能用敘事方式,只有藉著敘述,而非藉著只能夠進行討論的哲學或神學闡述。討論不是耶穌會的作風,分辨才是,當然,分辨過程預先假定也包括討論的部分,但其中的未知部分不會被劃定界限,以不讓思想畫上句號。耶穌會士必須是思想尚未完善、思想敞開的人。耶穌會曾有過思想封閉、僵硬的時期,更注重學問研究和苦行而非神秘思想,這種扭曲產生了 Epitome Instituti(耶穌會綱領)。」
教宗這裡所談的是耶穌會在二十世紀使用並重新修訂的行為準則,這本簡章被當作會憲的替代品。耶穌會士的培育有一段時期受這本準則的塑造,乃致有些人從未讀過會憲──這個當仁不讓的創會文本。在教宗看來,耶穌會在那段時期,修會規律差點淹沒了修會精神,陷入了詳述和過於闡明神恩的誘惑。
教宗續道:「不,耶穌會士總是不停地思索,以基督為中心,展望必須向前邁進的願景,他真正力量正正在於此。這股力量激勵耶穌會進行研究、創新並慷慨奉獻。可見,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須在行動中度默觀生活,更須與整個教會密切結合,視教會為『天主子民』和『聖潔的母親』,這需要百般謙遜、犧牲和膽量,在不被理解或遭誤解及誹謗的時候尤該如此,但這卻是一種更有成效的態度。讓我們想想過去因中國禮儀之爭、馬拉巴爾禮儀以及在巴拉圭傳教村所引起的緊張情勢,便可見一斑。」「我本人就是近期耶穌會遭誤解和遇上難題的見證人,在這些難題中,包括加發服從教宗這『第四願』予所有耶穌會士的那段艱困時期。然而,當時雅魯培神父(Arrupe)任總會長令我有信心:他是個祈禱的人,是花很多時間祈禱的人。我記得,他祈禱時就像日本人那樣盤坐地上,也正因如此,他有一種正確態度去作出適當的決定。」
「革新神父」伯多祿.法伯爾的典範
我很想知道,自耶穌會創立至今,會士當中是否有人對他影響特別大。於是我問教宗,若有的話,他們是誰?為甚麼?教宗先為我點出依納爵和方濟各沙勿略,然後詳細談論一個耶穌會士都知道但卻鮮為其他人所知的另一個人物,他就是真福伯多祿.法伯爾(Pierre Favre,1506-1546年),一位薩沃依人。法伯爾是聖依納爵最早的夥伴之一,二人在索邦(Sorbona)求學時同住一個房間,他是依納爵的第一個室友;而住進同一個房間的第三個室友是方濟各沙勿略。法伯爾於一八七二年九月五日被教宗庇護九世(Pio IX)宣佈為真福,列聖品案目前還在進行中。
教宗向我提起法伯爾回憶錄的一個版本,是他當阿根廷省會長時請兩位耶穌會士專家米格爾.菲奧里托(Miguel A. Fiorito)和海梅.阿瑪德奧(Jaime H. Amadeo)負責編輯的,但教宗尤其喜愛米歇爾.塞爾托(Michel de Certeau)編輯的版本。我問他為何被法伯爾所打動,這個人物的哪些特徵讓他印象深刻。
「是他與所有人的對話,即使是最遙遠的人和對手;他有純樸的熱心,一種也許有些天真,卻能隨時臨在的態度;他注意內心分辨,又是個能作重大決定且又能夠保持溫和、親切的人。」
從教宗方濟各數說著他所佩服的耶穌會士這些個人特徵時,我了解到這個人物為他實在是生活典範。米歇爾.塞爾托稱法伯爾是「革新的神父」,說在他眼裡,內在經驗、信理表達和結構改革彼此不可分離。
教宗也對耶穌會創始人依納爵羅耀拉(Ignatius of Loyola)作出闡釋:「依納爵是個神秘主義者,不是苦行僧。當我聽到有人說神操只有在靜默中進行才是依納爵神操時,著實令我生氣。其實,完美的依納爵神操也能在日常生活和沒有靜默的情況下進行。強調苦行主義、靜默和作補贖的思潮是對神操的歪曲,它也在耶穌會,特別是西班牙修會中散佈。我則接近神秘學思想,就是路易.拉勒芒(Louis Lallemant)和讓.約瑟夫.蘇林(Jean-Joseph Surin)的思想。法伯爾就是一個神秘主義者。」
管理經驗
---------------------------------------------------------------------我獨斷專行和迅速作決定的方式曾給我
很大麻煩,令我被指控為極端保守分子。
---------------------------------------------------------------------
貝戈格利奧神父在耶穌會擔任過院長和省會長,他所接受的培育能為治理教會提供哪種經驗?耶穌會的管理風格是長上做決定,但也徵求「參議」的意見。於是我問教宗:「你認為自己過去的管理經驗能運用在目前普世教會的的管治上嗎?」教宗嚴肅地略作思索,卻十分平靜地說:「說實話,我在耶穌會做長上時並不常作必要的諮詢。這不是好事,作為耶穌會士,我最初的管理有許多缺點。那是耶穌會的一段艱難時期:整整一代會士都消失了,為此我尚很年輕就當了省會長。那時我才三十六歲,真是瘋狂;我必須面對困局,我以生硬且獨斷的方式作出決定。但我必須補充:我一旦將事情委託給人,就全盤信任他,除非他真的犯了大錯我才會作出指責。儘管這樣,人們對專制做法始終感到厭倦。我獨斷專行和迅速作決定的方式給我帶來很大麻煩,亦令我被指控為極端保守分子。我在科爾多瓦(Cordova)時內心曾有過嚴重危機的時期。你看,我當然不是真福伊梅爾達(譯註:她是位非常虔誠溫柔的小女孩),但也絕不是右派分子,是我獨斷專行作決定的方式造成麻煩。」
「我把這些生活經驗說出,好使人瞭解甚麽是危險的事情。隨著時間過去我學會許多,上主亦讓我透過缺點和過失掌握管治的學問,因此,我任布宜諾斯艾利斯總主教時,每隔半個月就召集六位輔理主教開會,一年當中與司鐸議會碰面數次。會上提出問題並開放討論空間,這為我作出最好的決定很有幫助。然而,現在卻聽到有人對我說:『別過於諮詢,決定就是了。』但我卻認為諮詢極為重要。例如:樞密會議、世界主教會議使諮詢起到真實和積極作用,不過,在形式上不必僵硬,我願意繼續實際而非流於形式的諮詢。八位樞機的諮議會、這個『局外人』的顧問團不只是我的決定,也是樞機的心願,是選舉教宗會議召開前全體樞機大會上表達的願望。我希望它是實質而非形式化的諮議會。」
「與教會同心同德」
接下去是關於教會的主題,我問教宗方濟各,聖依納爵神操中「與教會同心同德」到底有何意義。教宗毫不遲疑地以一幅圖像去闡述:「我所喜歡的教會圖像是天主的忠實聖民,我經常使用這個定義,它也是《教會憲章》第十二號的定義。隸屬一個子民具有強烈的神學價值:天主在救恩史上拯救了一個子民。若不隸屬一個子民,人就沒有十足的身分。沒有一人能作為孤立的個體而能自救,天主卻顧及人在團體中建立相互關係的複合情節,將我們吸引到祂那裡。天主進入人與人的互動中。」
「子民是主體,教會是在歷史中行走的天主子民,有甘甜苦樂。因此為我來說,與教會同心同德就是成為這個子民的一份子。全體信徒一起,在信仰上是不能錯誤的,全體子民一同行走,藉著超性信德,展示出這個『信仰的不可錯誤性』。這就是今天我對聖依納爵談及『與教會同心同德』的理解。人們同主教和教宗之間的交談一旦走上這條路,這交談便是真誠的,有聖神護佑。與教會同心同德並非只涉及神學家。」「如同聖母瑪利亞的情況一樣:若想知道她是誰,就去問神學家;若想知道如何愛慕她,就須詢問民眾。正如《聖母頌詞》中所表達的,聖母以民眾的心愛了耶穌。因此,我們不能以為『與教會同心同德』只是與聖秩部分的教會相關。」
教宗停頓片刻,為避免誤解而更直接的補充:「顯而易見,須十分當心不要以為我依照大公會議所談的全體信徒的不可錯誤性是一種民眾主義;不是的,這是牧人和子民一起組成的天主子民教會,聖依納爵稱之為『聖潔母親聖統教會』的經驗。教會是全體的天主子民。」「我在天主子民身上看到聖德,是日常生活的聖德。馬萊格提出一個『聖德的中產階級』,我們都屬於其中。」約瑟夫.馬萊格(Joseph Malègue)是教宗的心愛法國作家,生於一八七六年,死於一九四○年。教宗尤其喜愛他未完成的三部曲《黑石頭:得救的中產階級》(Pierres noires. Les Classes moyennes du Salut)一書,一些法國評論家稱馬萊格是「公教的普魯斯特」。
教宗接著說:「我在忍耐的天主子民身上看到聖德:將子女撫養成人的女人、為家裏賺得麵包的男人、病人、年邁的神父,他們有很多創傷,卻仍帶著微笑,因為他們服事了上主;還有埋頭苦幹的修女,她們在隱秘中活出聖德。在我眼裡,這是大眾的聖德。我常把聖德與忍耐相聯:忍耐不僅是hypomoné(譯註:新約希臘文,意為『苦扛』),把生活上的事件及境遇背在自己身上,也是日復一日向前走的恆心。這也是聖依納爵所說的戰鬥教會的聖德,是我父母和使我獲益良多的羅薩祖母的聖德。我的《日課》中夾著羅薩祖母的遺囑,我常拿出來閱讀,我視它如一篇祈禱文。祖母是個身心均受過很大苦楚的有聖德之人,始終勇往直 前。」
「我們必須視與之『同心同德』的這個教會為眾人的家,不能只是容納被選中小部分人的小聖堂。我們不該把普世教會的懷抱貶為僅僅是保護我們平庸的安樂窩。」教宗繼續說:「教會是母親,是多產的,她必須如此。每當我發現教會的司鐸或度奉獻生活的男女表現不佳,首先會想:『這只是個單身漢,或者,這是個獨身主義者。』他們既不是父親,也不是母親,他們沒有能力賦予靈性生命。反之,當我讀到前往巴塔哥尼亞(Patagonia)傳教的慈幼會士生平時,看到的卻是有生命和有生育能力的事跡。」
「再舉出近日另一個實例:我給一個曾寫信給我的男孩打電話,這件事受到報界關注。我給他打電話,因為他的信寫得非常好,非常坦率,在我眼中是項奉獻生命的舉動。我又意識到他是個成長中的青年,他視我為父親,並向這位父親訴說自己生活上的一些事。這個父親不能說:『這與我無關。』這種能結果的成效令我感覺美好。」
年輕教會和古老教會
我繼續關於教會的主題,問教宗有關不久前的普世青年節:「這項重大盛事令人更加關注青年人,同時也關注新近建立的教會,她們是『精神肺葉』。這些教會能給普世教會帶來怎樣的希望?」「年輕教會發揚了信仰、文化和成長中生命的精華,與較古老教會所發展出的不同。在我看來,古老教會和年輕教會之間的關係就好似社會上青年人與老年人的關係:他們一起建設未來,青年人用氣力,老年人用智慧。當然,風險總是有的:年輕教會容易自以為是,古老教會則希望將自己的文化模式強加給年輕教會。但是,我們需要一起建設未來。」
教會?一所戰地醫院……
--------------------------------------------------------------------- 教會今天更需要醫治創傷和溫暖
信徒的心,關懷和接近他們的能力
---------------------------------------------------------------------
教宗本篤十六世宣布辭職時形容今日世界為突飛猛進的主體,並因信仰生活引起的重大問題而處於動盪中,處理這些問題需要體力和精神。我因應教宗剛才說的話繼續問:「在這歷史時刻,教會更需要甚麼?是改革嗎?你對今後幾年的教會有哪些願景?並『夢想』甚麼樣的教會?」
教宗方濟各回應:「教宗本篤作了一個有聖德、高尚和謙卑的舉動。他是天主的人。」教宗邊說邊對他的前任流露出深厚情感和無比敬佩。他續說:「我清楚看到教會今天更需要的是醫治創傷和溫暖信徒的心,關懷、接近他們的能力。我視教會如同戰爭後的一所戰地醫院。問一個嚴重傷者是否有高膽固醇和高血糖毫無意義!他的傷患必須先得到醫治,然後再談其餘一切。醫治傷患,治療創傷必須從低層做起。」
「教會有時把自己關在小事情、封閉在細微的誡律中。然而,第一個宣講的喜訊才更重要:耶穌基督救贖了你!教會的司鐸首先必須是仁慈的司鐸。例如:告解司鐸常會墮進過於嚴格或太寬鬆的困境裡。事實上兩者均不算慈悲,因為都沒有向人真正負責。嚴格者撒手不管,把責任推卸給誡律;寬鬆者撒手不管,只說『這不是罪』或類似的話。人需要陪伴,創傷須得到醫治。」
「我們應怎樣對待天主子民?我夢想一個母親和牧人教會。教會的司鐸必須是仁慈的,對人負責,陪伴人,如同慈善的撒瑪黎雅人那樣,洗淨他的近人,減輕他的痛苦,這才是純正的福音。天主比罪更強大,組織和結構改革是次要的,意思是以後會隨之而來。首要的革新必須是態度上的革新。福音的服務者必須是能夠溫暖人心、在黑夜中與他們同行、懂得交談且進入他們的黑夜,但在黑暗中卻不迷失自己的人。天主子民要的是牧人,而不是像官員般的聖職人員。主教更應是能夠耐心扶持天主子民,讓他們按天主指引的路行走的人,不讓任何一個人落在後頭。他們也要懂得陪伴常會鑑別新道路的羊群。」
「與其只作敞開門戶接納別人的教會,我們不如設法成為尋找新道路的教會。這個教會能夠走出自己,走向不與她往來、離開她或對她不聞不問的人。有時人離開教會是出於某些理由,要是這些理由備受理解和重視,就能使他們返回教會。但這需要膽量和勇氣。」
我順著教宗的話題,提到有些基督信徒的生活為教會而言並不正常,或處於複雜情況,這些信徒似乎正處在敞開的創傷中,我提到這包括離婚再婚者、同性的結合以及其他身處困難境地的人,又問在這些情況下,如何進行牧靈傳教工作?關注點又是甚麼?教宗明白我的問題,並回答:
「我們須於每個街角宣講福音,宣講天國喜訊,用我們的宣講醫治各種疾病和創傷。在布宜諾斯艾利斯時我常收到同性戀者的來信,他們是『社會上受傷的一群』,他們告訴我,覺得自己總是備受教會責備。事實上,教會無意這樣做。我從里約熱內盧的回程中曾說,要是一個同性戀者有善意並且尋求天主,我哪有資格去判斷他。我這話是《天主教教理》上的話。宗教有權利表達自己對服務人群的看法,可是天主在創造宇宙萬物時給了我們自由:在精神上干預一個人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一次有人用挑釁的口吻問我是否贊成同性戀,我於是反問他:『請告訴我:天主注視一名同性戀者的時候,是以慈愛看待他呢,還是排拒他、譴責他?』我們必須重視人,這樣我們才能進入人的奧跡。在生命中,天主與人同行;我們也應從開始因應他們的狀況陪伴他們,並須以慈悲的心來陪伴他們。一旦做到這點,聖神就能啟發司鐸說出更合適的話。」
「按每一種情況評估、為一個尋求天主及其恩寵的人分辨出最好的辦法,這也是告解聖事的偉大。告解亭不是酷刑室,而是上主慈悲為懷激勵我們盡力做得更好的地方。我也想到在婚姻上失敗並曾墮胎的一個女人。這個女人已經再婚,現在與五個子女安詳度日。墮胎是她背上的沉重包袱,她已經誠懇地懺悔而且願意繼續度基督信仰生活。告解司鐸要怎麼做呢?」
「我們不能只固執於有關墮胎、同性婚姻和使用避孕方法的問題,這是不可能的。我對這些事談得不多,為此亦受到非議。可是在談這些事的時候,我們需要連同背景一併考慮。再說,教會的看法我也知道,我是教會的兒子,但不必總是喋喋不休地談這些問題。」
「教會的信理和倫理訓導並非完全同等的。牧靈傳教,不能執迷於傳授大量不連貫的教理,強人接受,傳教的宣講須體現在更能激勵人和更具吸引力的實質性和必要的工作上,就如在厄瑪烏的門徒們心上燃起熱火那樣。因此,我們必須找到新的平衡點,否則教會的道德建構會像紙糊的古堡那樣坍塌,失去福音的馨香。合乎福音的建議必須更簡明、深入、有感染力,再由這些建議總結出道德結果。」
「說這話時,我也想到宣講和我們宣講的內容。好的、真正的講道必須從第一個喜訊,從救恩喜訊開始,沒有比這喜訊更牢靠、深邃的內容。然後是要理講授。最後才能得出道德結果,但要把宣講天主救恩的愛放在道德和宗教誡律前面,然而,今天這個次序有時被顛倒。彌撒講道是衡量牧人有否關懷子民,與他們相遇能力的試金石,因為宣講的人必須認出他團體的心意,好知道在哪裡找到對天主的熱切渴望。因此,相關的福音訊息不能被簡化為幾方面,因為分開闡釋福音不能反映耶穌訓誨的核心。」(未完)
- 來源:梵蒂岡電台╱天亞社轉載;
參考《人籟》《America》
- 圖片:天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