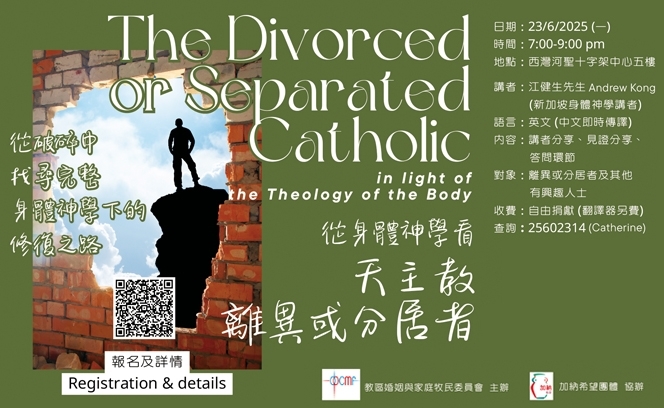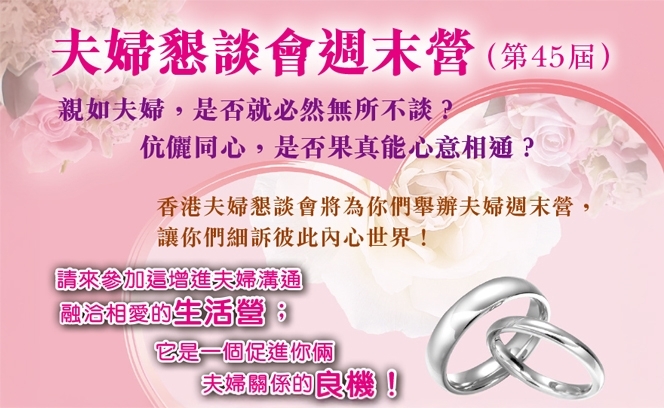【在人間】放鬆
中國人教人努力很誇張。蘇秦未發跡時潛心苦讀,頭懸樑錐刺股,成了千古楷模。可惜智慧不等於記憶儲備競賽,要格物明德,沒有優悠的心胸,思維模式大多必如單向街,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僵化而死硬。近世我們在哪個領域缺過這等氣味?人人都怕孩子輸在起跑線上,但有無想過,我們對小孩的「催谷」,常不無偏頗, 給他們進的「補」,有多少未見其利先見其害?
中國文化博大精深,乃因能包容對立。一旦單向,必令不識者嚇死識者笑死。小時聽人誇誇其談,說寫字時人在背後用力扯筆管也抽不動才算夠功力。許多書教國畫,說定得從工筆入手……幸而我走運,算是在合格的師門受過教,深知書畫筆劃的力並不是物理學上的力,寫字也不是打拳,哪有死力可拚?自古有道「腕不虛則畫非是,畫非是則腕不靈」,和提琴高手一樣,書畫家的腕一定務虛不務實,行筆都不拘一格,寫成怎麼樣,全乃興之所至,意到筆到。學書入門時得平腕、虛掌、實指、讓筆管豎直,為的是學會讓筆力內歛,但不筆筆中鋒並非罪大惡極,宋以後,許多大書家常側鋒取勢,難道就不入流?且一到行草,筆走龍蛇,拘謹反是大忌。說意筆的根底是工筆則更外行。由晉到宋,昔人花了幾百年才在五代末年從工筆重彩中突圍而出,文人畫就是在這變革中成就的。工筆求圓滑,意筆卻講韻味,講蒼拙。初學時得學會把筆劃寫得有如屋漏痕,浸潤而力透紙背,得學會讓整個手臂的力能透過筆管集結在筆鋒。但得其要領,便要學會用筆像拿筷子挾菜一樣自由,揮灑自如。人要做成甚麼,必得著力,也必會緊張,但若要成事,卻不能用死力、蠻力,同時要學會放鬆,最用力最用功時也得氣定神閒,游刃有餘。自古說「文武之道,一張一馳」,有人認為兩者輪流坐莊即可,其實大謬不然。你要得其所哉,便得張也是馳,馳也是張,文武同一。這難嗎?為未入門者說很難,為行家來說卻自然而然。即使筆下的題目有多沉重,只要一下手,最好有若遊戲人間。不如臨大敵,才有希望做出水準來。
看書畫高手揮毫,看獨奏會上大師運弓,不必看畫聽曲,單是動作本身,就是至境。我得慶幸,自小學畫,老大陪兒子學琴,居然學會了欣賞世上最美妙的東西。道之所存師之所存,名師未必出高徒,但起碼能讓你知道,甚麼才是正道。人學甚麼不一定要做甚麼,但知道該怎麼發力才不貽笑大方,卻可令你對許多事情一理通百理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