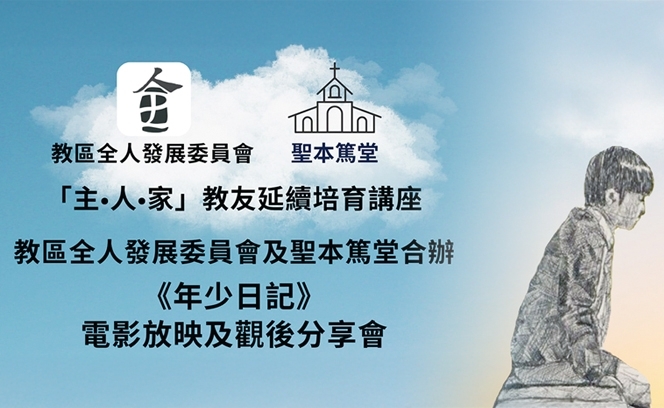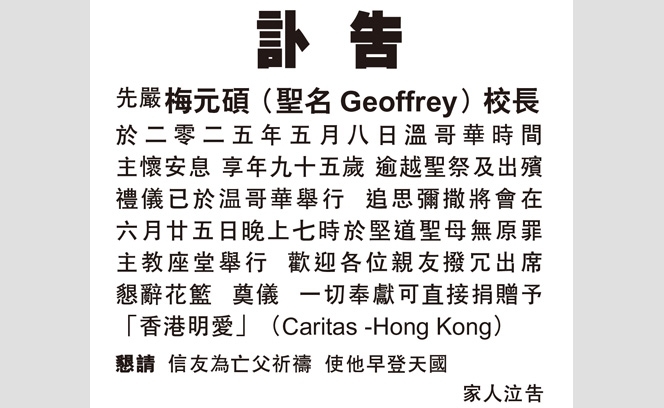十年後的十日——
十年前首次踏足泰澤團體(Taizé)並在那裡生活體驗了三個月,當年負責接待亞洲青年的若望. 瑪利修士(Jean-Marie)在四月初首次到訪香港十日。我沒有跟著他到訪每個場合,以下只是重遇修士的點滴反思和分享。
二〇一六年泰澤團體提出了《慈悲的勇氣》的五項建議,即託付自己於慈悲的上主、再三寬恕、獨自一人或與少數人走近不幸的境況、使慈悲及至社會層面,以及慈悲對待整個世界。在四月十六日的道風山退修的自由分組討論時,最多參加者討論第三個建議,大家都笑說在香港太多「不幸的境況」。有參加者問:「為甚麼慈悲都需要勇氣?」修士沒有直接回答,卻更巧妙地反問各參加者。各人討論後都發現,在生活上實踐慈悲, 比想像更困難:在車上讓座會遭到拒絕、走近天橋上衣衫襤褸的弱小者也膽顫心驚,甚至已認定自己是個心硬的人。那麼,勇氣是必須的。
修士對香港的關注
雖然初次到港,本身是紐約人的若望.瑪利修士打趣地說,自己首天看到維港兩岸的霓虹燈已仿似回到親切的老家。香港人的「機不離手」也使他感到這個城市裡的人的匆忙。他應教區青年牧民委員會邀請主持「信心在人間」避靜,看見年輕人都拿著手機看聖經,他既大開眼界卻又包容接納,更笑問大家能否在不同的手機品牌看出不同的聖經!
修士很關心香港社會的情況,特別是年輕人的情況。「請給我說點關於雨傘運動的事」是他最先的提問。在港期間,不論是年輕人的迷失和氣餒、香港社會的問題和矛盾、香港及中國教會的現況、中國人╱香港人的習俗,他都逐一細心聆聽過。我還口多,說了個人的想法:「不去認識、不去關心、不去信賴,都比較容易。可是我『仍然是要相信,這裡會有希望』」。
四月十二日晚,若望.瑪利修士到聖博德堂主持晚禱。在路上走著時,他也留意四周的公營房屋跟大型商場產生的對比。那夜正掛黃雨警告,恰巧路旁有個呆站著的伯伯,像是要向路人要點甚麼,修士注視著他,相信也切身處地感受香港的情況。
修士為人
若望.瑪利修士在泰澤主要負責音樂和禮儀,每日三次的祈禱和泰澤團體灌錄的唱片內的詩節很多都是由他領唱。客觀來說,他在泰澤團體是舉足輕重的。他天賦有一把動人的歌聲,每次聽他歌唱都特別容易感到上主的美善。然而他從不會主動介紹自己的崗位,更從不會以自己天賦歌聲而自誇。在不同的祈禱聚會或避靜時,他總是坐在人群中跟大家一起練歌,更經常誠懇的讚賞大家唱得美妙動聽。
另外,若望.瑪利修士亦很融入香港文化。有一次,我陪伴修士去拜訪在長洲的神長。他說要做普羅大眾做的事,就是「搭慢船」入,還在戶外大牌檔吃了個魚蛋粉,「很開心可以做香港本地人做的事」。因走上靜修院時行錯了路口,我向路旁的小店問路,修士向老闆用純正的廣東話(甚至帶點長洲人的爽朗)說「唔該」!泰澤修士的語言能力都極高, 好幾次祈禱時,修士在大家毫無心理準備之下以廣東話起唱《讚美我上主》和《不再有憂慮》,令人驚訝。
- 泰澤團體於本年八月十一至十四日假長洲舉行東亞青年聚會,此前泰澤的若望.瑪利修士四月訪港,了解本地的情況 —— 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