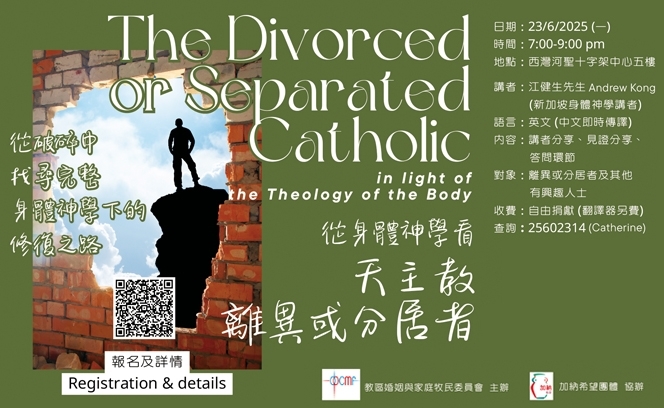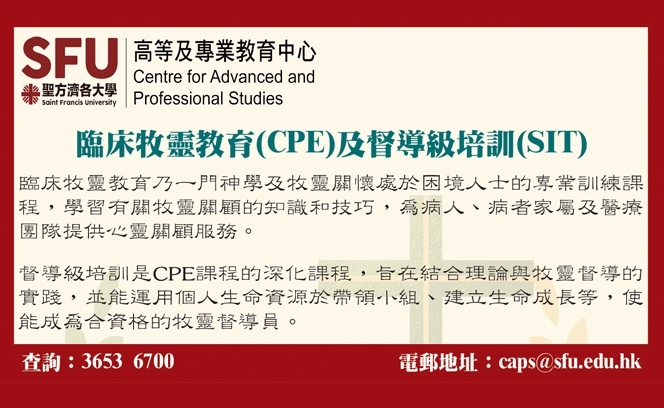【在人間】也說「存在」

《楚辭》有兩闕最重要的賦,一曰《天問》,一名《離騷》。《天問》其實是問天:這世道為何總是顛倒黑白,忠不必用賢不必以?人在處處碰壁時總免不了追問「天理何在」?《離騷》即離別時發的牢騷和感喟。個中的「離」不是與情人「執手相看淚眼」的難分難捨,而是屈原投江自盡前對人間的回望。人面臨生死抉擇,便得直面生存的真諦。哈姆雷特說: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問題。」這話,莎士比亞寫的是To be or not to be, that’s a question。「生存還是毀滅」是意譯,直譯是「活還是不活」,更準確直解其實是「存在或不存在」。中文說的「存在」在英文是Being, 它是甚麼意思?若我們說it is something, Being就是聯繫動詞is 的名詞化,不去意指賓詞something,is 就成了Being。黑格爾說, 只有當古希臘人提出Being 這概念時,哲學史才真正開始。「存在」(Being)是一切概念中最基底的概念。人的思索離不開概念推演, 而生存的人才可思索,生存就是思索的主體「存在」於世間。若我不「存在」,對於其他的「存在」便不能思索。那麼,世上若有公理存在,要推敲其來由,便得有一個早於我,大於我,能生出所有「存在」的「存在」,這除了所有古文化都最後指向的「上天」,我們還能到哪兒去追問呢?活不活?怎麼活? 是「存在」探索的關鍵。誰說我們古代沒有哲學?屈賦的底層,不就有個很嚴整的「存在論」嗎?當然,感喟性質的歌吟不等於實斧實鑿的研究,我們中國文化對形上問題從來都是「差不多」了事,漢以後西來的佛學之所以能在中土找到市場,是因為補了儒學這方面的疏陋。但原始佛家也有和孔學近似的實用心態,碰到與修行實踐無關的論題,釋迦牟尼也未必如其先輩吠陀學人般有興趣查根問柢。佛學後來在中國化為一切隨心隨意的禪學,其實是很有中國特色的。
存在論又叫本體論,在西方學術是大學問,不但門派森嚴,且深不見底, 許多人窮盡一生也不得要領。竊以為進入其間,有如用人有限的智力去尋求人面對宇宙底蘊時認知的無限可能性,誰也不可能有甚麼最後定論,但我輩若能在前人探索的正反經驗裡得到一點啟發,說不定茅塞頓開。本體論這名號是中世紀才出現的,但其思維本色,早在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手上已開始成為西方思辯正宗,認為有識者探討的該是具 有普遍意義的本質而不是表象。面對問題必先從概念入手,理清定義,然後把要面對的問題放進自家推敲出來的概念演繹裡,以此釐定性質,得出結論。這思維方式幾乎成了千百年來「有識者」的主流思維套路,既造就了啟蒙時代理性的覺醒和後來法國人牽頭的社會改革,也令無數類型的專制甚至納粹式極權振振有詞。想不讓人牽著鼻子走,便得學會「理解」這些「精英」們一言九鼎的破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