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本是同根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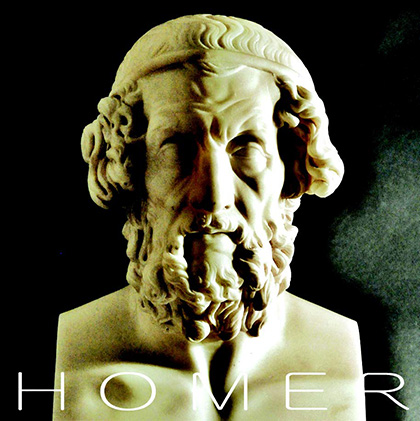
人發明哲學,非為玄談, 而為解惑。但書和書總在對話,後學亦只能在古來高人的筆戰砲火中匍匐前進,學會在相互衝突的意見中練就一雙利眼。古希臘人愛說的「邏各斯」(logos)原指「話語」,亦指分辨真偽的能力,分析 、說理須依循的「規則」。這字派生出「邏輯」(Logic)即「理則」,後來亞里士多德區分了各種知識範疇, 表示學科的字尾(-logy)也出自它。在中世紀,它變為拉丁的r a t io,英文「理智」(re a s on)與「理性」(Rationality)的字根亦本於此,可見是西方文化的重要概念。但與之相對的「秘索斯」( muthos )也是西方文化的另一基石。據說這字的詞根與古印歐語的mu有關, 原指合攏雙唇,發出低沈的呼聲,令人想起《吠陀經》說,「唵」這個音節在印度古時被認為是宇宙中所出現的第一個音。 佛教受印度教影響,也認為這是個聖潔音節,不少密宗咒語都以「唵」字開首。筆者識淺,不敢胡亂揣度兩者的關係,但梵文是古印歐語的一支,古希臘人和古印度的亞利安人有相同的神秘體驗並不稀奇。這近乎「 閉嘴」 的音估計是古代祭司在祭祀時神秘的「特殊話語」,與清晰言談一虛一實,異曲同工。言語是思想的載體,但真理有時盡在不言中, 否則老子為何說「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從這角度看,邏各斯和秘索斯其實一體兩面,這跨文化的識見有若精靈鹿角,是一服古老的智慧秘藥。
logos和muthos,這兩個字眼常出現在《荷馬史詩》上, 並無褒貶, 原都常作「詞」 、「 話」 或「 故事」 解。這史詩是遠古時口耳相傳的歌謠,是古希臘人的性情寶庫,愈近希臘的黃金時代則愈為世所重, 肩負的教化使命日重,便有哲人對其虛構性發難,開始了以科學的logos取代muthos 的進程。哲學也由是誕生,在柏拉圖之前歸結為巴門尼德的「存在論」,給以後的西方哲學奠定基調。而標榜真實敘述的Logos 試圖取代專事神話式敘述的muthos的努力,也引發了曠日持久的一波又一波的啓蒙思潮,一直風靡到時下。由公元前六世紀起, 出現了 大量以散文寫作的自然哲學家、歷史學家、醫學專家和廣義上的學問家,他們幾乎「一哄而起」,借助邏各斯的精確駁斥秘索思的詩性和神話思維的荒唐和虛假。在柏拉圖以前,執筆為文者都出口成詩,即使天文學著作也由詩體寫成,懷有詩樣情懷者才有幸闖蕩文壇似乎成了自古傳下的慣例。但到了柏拉圖時代,雖然柏氏本人詩興十足,以與荷馬分庭抗禮為宿願,但時移勢易,也由他開始,哲人都以理性自許,而索福克勒斯等悲劇詩人也深受智者的影響, 仰慕邏各斯的力量,開創了寫作頗具智辯風格的大段演說詞的風氣。柏拉圖強化了前輩學人對muthos 與logos 的區分。他看到了神話( m y t h o s ) 與論述(logos)的不同,但,這兩種傳意傾向其實本是同根生,真的能輕易切割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