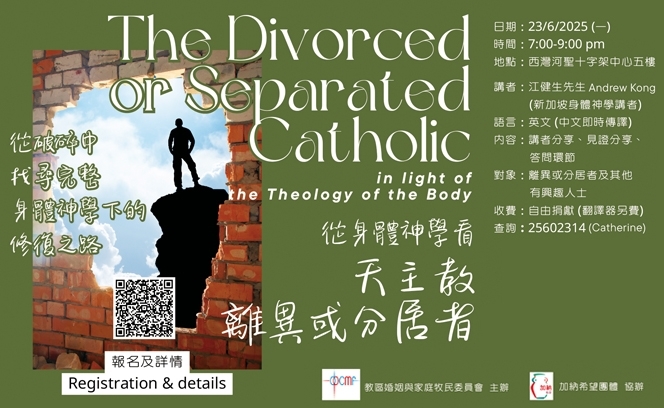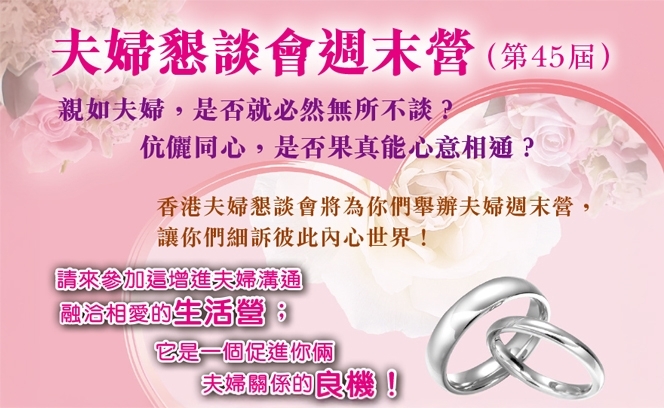【在人間】書道

朋友學書法,老師從甲骨文入手,繼而小篆大篆, 到漢隸北碑,然後轉入唐初四大家, 讓學生把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褚(遂良),的楷書都寫上一輪,再及宋元行草… …天天泡浸在筆墨裡兩年,然後才挑自家最喜歡的碑帖再行深造。這教法等於先讓學生在書法史上全面涉獵,試著手摹手追,但如漁翁撒網,每家每派都淺嘗即止,所得當然不深,但好在先有個宏觀認識,再選定某家來作微觀研究,其實是很好的方案。只不過,教者要有通識,還幾乎要古今十八般武藝全能,學者也要心有靈犀,教者和學者都講心力和學養,都不易為。但普天之下,有甚麼學問或技藝是「食磚豆腐能成仙」的呢?
朋友問世上有畫家、作家,有只靠書法立足的「書家」嗎?我笑了:書法史上並無白丁,古時大書家定是大官僚,不是說做不了大官便寫不好字,而是我們中國人的歷史上能位列廟堂的,除了官,還是官。近人斥之曰「官本位」,但罵歸罵,如今還仍是常態。唐時曹霸擅畫馬,杜甫寫詩稱讚,劈頭便說「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為庶為清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猶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瞧,曹畫能入大詩人法眼,先因顯赫世系,本人還是「將軍」。唐時門閥觀念仍頑固,上品無寒門, 下品無士族,無官二代三代背景便不足觀。勢利雖可惡,卻是人之常情。
但世風總在變異,同是官本位文化,不同世道卻有不同色彩。元以後,程朱理學成了正宗,官樣文章便愛板起臉孔盡說些偉光正廢話,在仕途之外的在野文化不堪納悶, 便自行發展出另一套清流文化。北宋以前, 藝文有兩條路線可走,文以載道當然是正宗,但也認為藝文的純美感也是自然之道, 也同樣是值得推崇的道統。但南宋開始冒頭的理學便只提倡前者而把後者當作歪風。程朱本和蘇東坡是同時代人,但到南宋,理學還未成大氣候,元代科舉開了把朱熹的經書註疏當準則的先河,一味強調載道,明和清的官家文化自然不會出現漢晉詩賦和唐宋詩詞那種豐富的取態,連評定藝文,也政治行頭。例如北宋大書家有四,蘇(軾)、黃(山谷、)米(芾)、蔡(京),但因為蔡是「奸臣」(王安石時代極風光),他的字也無人再提。其實就書論書,他的字相當不錯。
國畫和書法的傳統理論都認為字和畫都心肖其人,也許對。但我就見過許多德行並不佳的人,卻有相當不俗的書畫造詣。一個人對美感的感應未必定和道德定能掛勾,何況何謂有德何謂失德,其實也不易有非黑即白的定論。如果書畫之道和人的性格有關,但性格和道德卻未必有關。同是性格豪邁的人,可以做英雄,也可以做賊頭,若他們都有書畫天份和好的師承,筆下的東西,從純藝術角度看,未必受因心術而有高下之分。中國古來把藝文學術的評介與泛道德說教混為一談,看起來很有「正義」感,其實是大有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