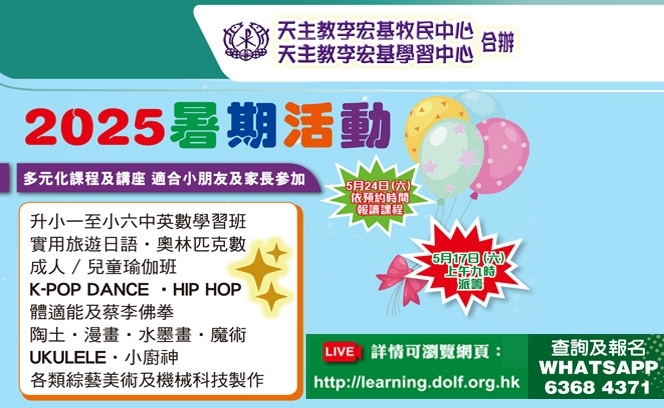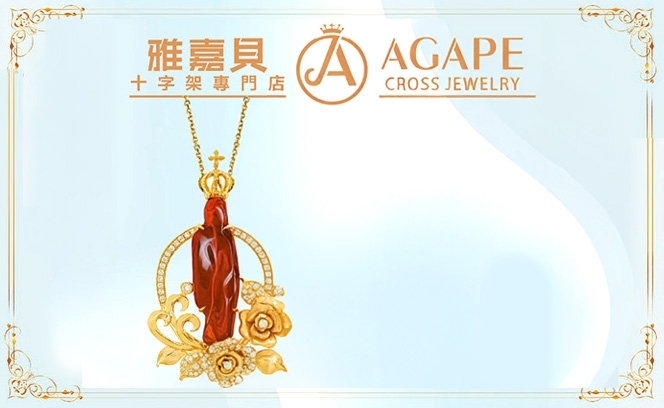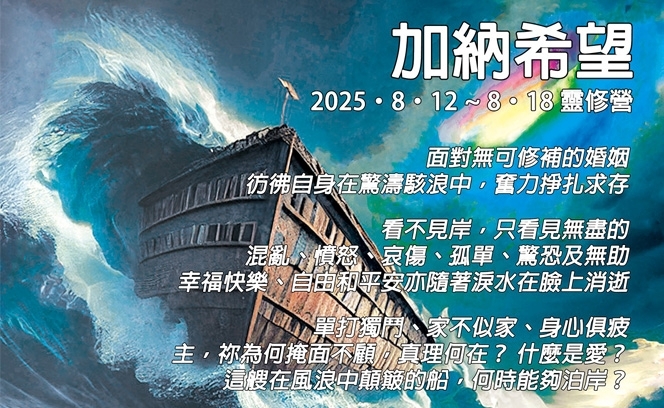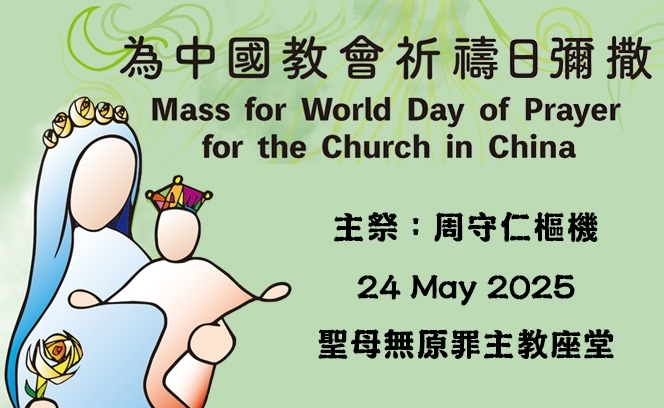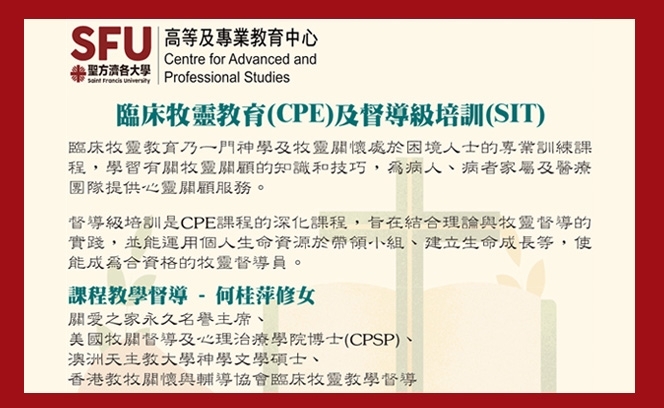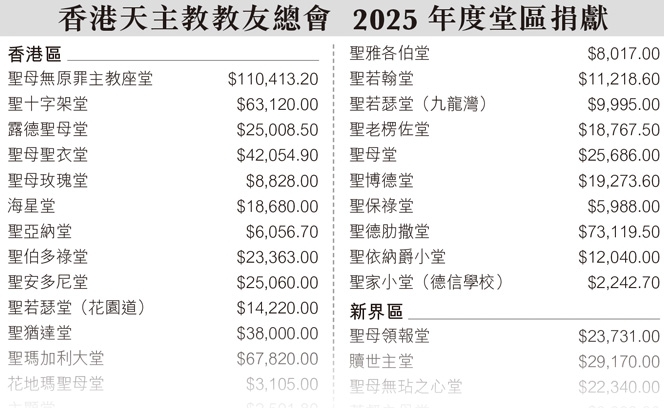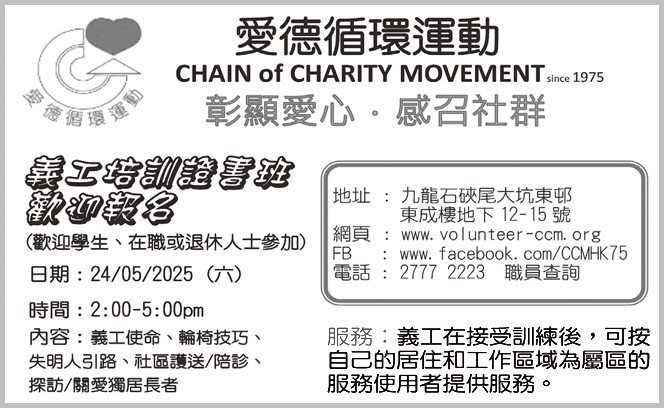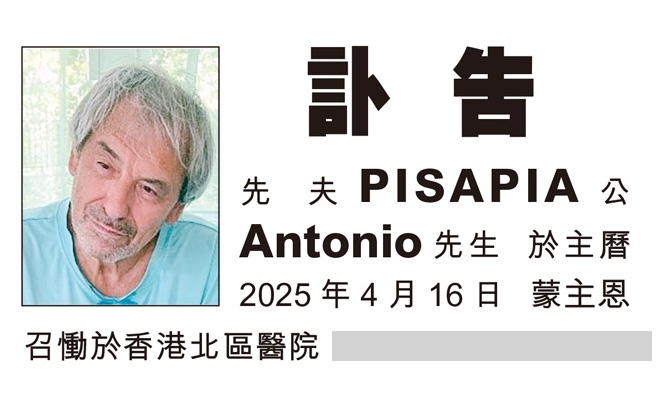【在人間】層累的想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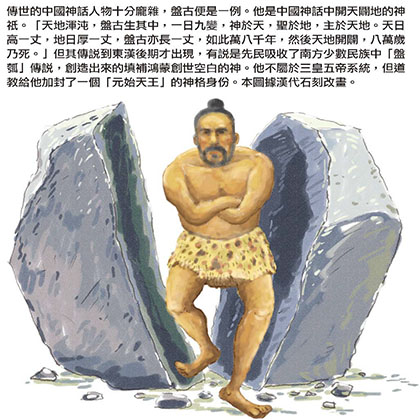
有說中國神話不成體系。問題是,所謂「體系」指的是甚麼?據說古希臘文「神話」的意思是「說話」。人有見識有意向, 都得釋放,嘴巴上釋放的是說話,身體力行的釋放是行動。行動不易有效,用說話來釋放不可名狀的意向更不容易,因此才有神話,也注定了神話和現實間必有莫大距離。神話因時因地不斷被改寫,一定支離破碎,是以不存在一早便有的「神話」體系。神話故事能成書,定經多年口耳相傳,然後有人整理出來。而如何整理,都服從於成書者所持的意識形態需要。所謂成「體系」不過是把眾說紛紜的故事互相協調,使之口徑統一。因此,除非當時的信仰生活已整合為族群大致的通識,否則就無所謂體系。
希臘——羅馬神話,北歐神話其實也有許多個不同的闡述系統,同一神話人物留下來的足跡也複雜異常,集大成者寫下的是「史詩」,神話和史詩不錯互相交叉,但並不等同。神譜能出現,是因為出現了在信仰上作綜合大敘述的推動力。這或許出於世俗生活對家門文化的需要,也或許出現了宗教整合趨向。《聖經》、《古蘭經》和《吠陀經典》等確比我們現在能接觸到的中國神話整齊,但這些文本都有牢固的宗教背景。由歷代有濃厚宗教色彩的學人對傳世古代文本經過嚴格挑選而成,且從歷史的軌跡看,常不是由神話文本產生神學,而是先有宗教,然後由宗教信條及禮儀需要去挑選合適的傳世故事文本,之後的解釋也不一定是由經文故事推演出教理,更常是以教理去解釋經文。中外古代文士都最愛給古老經典作新註解來宣揚己見,是因為「托古改制」最名正言順。在中國,秦漢以後的把神話重新整合蔚然成風,剌激了儒生們弄出了三皇五帝的世系。但中國文化沒有宗教,統治者也不需要宗教,因為我們的文化其實不需要有個作為萬事起源的人格化主宰,亦不需要尋找萬事萬象背後演化邏輯上的第一因,不鼓勵形上深思,不主張查根究柢。「天子重賢豪,文章教爾曹」,一切是非黑白,有當朝皇帝一錘定音便足夠。民間信仰只需發明出一個玉皇大帝便可把三山五岳或滿天神佛搞定。就像在現實世界,人們只盼望有個想像中的仁君或包青天便萬事大吉。
如今我們讀到的中國「神話」大多不是先秦產物,而是後代以新的文化元素竄生出來,嚴格地說,時序基本都是錯的,以此為基礎的「體系」只是後世儒生想像的層累。從顧頡剛開始, 很多代中國神話學學者其實已經把很多故事和人物的具體時序大概釐清了。這反而讓我們知道, 其實上古時代神話體系是大致存在的,卻和時下一般人眼裡的伏羲女媧盤古之類的故事差別很大。它當然不是一套能和荷馬史詩之類的神話可以類比的東西,但這不打緊,我們還是可以像西方近百年的古典學者一樣,在許多幾乎湮沒的古代傳說和出土文物中好好地理解它們的來龍去脈,其要旨不是要恢復一套恢宏的神話史詩,而是憑這理解我們祖先的心跡,進而理解我們面對的現實中的所謂民智的一團渾沌的來龍去脈。(神話與真實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