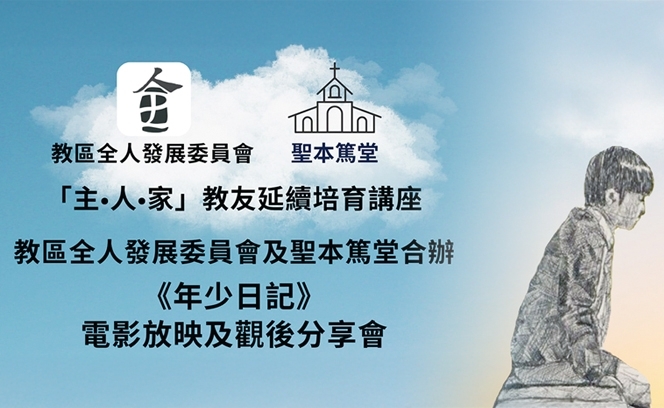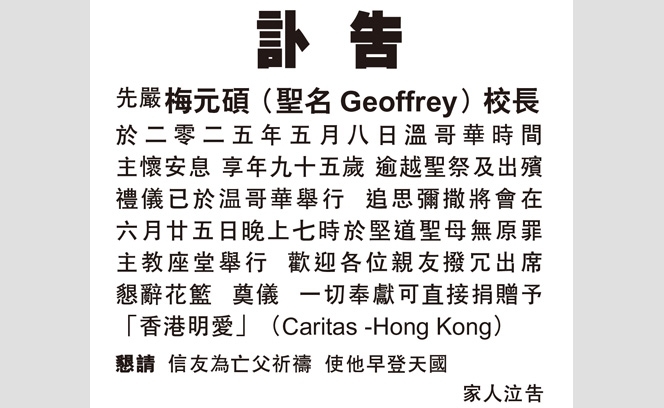【在人間】悲劇的誕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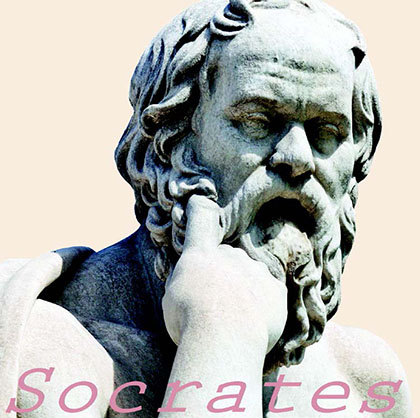
人來到世上便得面對紛爭。熱血和自以為的正義常使人自覺或不自覺地選邊站,各式各樣的「道理」充斥輿論市場,還少不了各種大敍述在背後支撐……書呆子要不人云亦云,唯有在書海上下求索。但「書和書總是在對話」,不同立場不免黨同伐異,即使同一派系甚至同一作者也常自相矛盾。柏拉圖對西方思想的影響有如孔子之於中國文化,他傳世的對話錄就充滿諸如此類的掙扎,令人不禁深思:怎樣才能把昔人讀懂?走出他們留下的思想迷宮?
就從柏拉圖全集的首篇說起吧。翻開《申辯篇》,柏氏一下筆便是蘇格拉底受審, 一齣迄今從未演完的悲劇亦由此開場:思想自由與政治現實能共處嗎?自由表述與公權力碰撞使蘇格拉底成為後世政治抵抗的標竿人物。但讀《申辯篇》,蘇從未涉及捍衛言論自由的高論。他主張的是受檢視的人生才有價值,即認為人需持恆釐清自家的思維才值得活。後來寫《平庸之惡》的漢娜.阿倫特把這意思簡述為:人有別於動物的是會思考,思考才可讓我們拒絕罪惡,遠離作惡。請注意,言論自由不是蘇格拉底要爭取的目標,但若無言論自由, 他當然仍可獨立思考,但不能在公共場所討論,其思考便成了獨腳戲,他提倡的辯證法便被廢武功。於是雅典公民的表達自由雖不必由他力爭,卻是他生存的前提。也許他認為這不證自明,不必唇舌,但讓他受審和致死的,卻正是這不曾爭抝的爭抝。柏拉圖實際上揣出的問題是:為何世上第一個最自由開放的社會竟把自由表述意見的智者判死?有說蘇的申辯是反客為主,逼使雅典全城受審,將雅典的民主也拱出來審判。這說明民主和自由並非同一回事,而要蘇格拉底閉嘴的,正是雅典的民主。也許柏拉圖確有把矛頭對準這一點之意,但這在記述蘇格拉底之死的三篇對話錄中都不是主題,而在他較晚的著作《理想國》才可看清眉目。
蘇格拉底被控的罪名是不信城邦供奉的神明和毒害青年。蘇並非無神論者,雅典其實也無既定的宗教信條和禮儀,一般人的信仰來自神話傳說,但神話式思維確支撐著䇄古至今的國族觀念和公權力的神聖不可侵犯。荷馬史詩《伊利亞德》首句是「唱出阿基里斯的憤怒吧,女神」……詩人呼喚眾神,以充滿浪漫色彩的詩句啟發和激蕩大眾同仇敵愾,城邦的意識形態充滿激情下暗藏的概念轉換。而蘇格拉底的智慧不含神喻,不說故事,以爭辯式的對話探尋經得起理性檢視的意向。正統的公民的忠誠及愛國心和道德判斷概由神話詩性思維形塑,蘇想要以一種新型態取而代之,他鼓吹的是理性的公民社會,以知識取代主張,理智取代信念。由是理性與維繫全城公民意向的虔誠之間的衝突頓起,蘇格拉底便成眾矢之的。
蘇格拉底說他不熱衷政治:「若我一早就活躍於政治,早就沒命了。為反對城邦行不公不法的事而違背大眾意志, 是沒人可活命的」。他提倡深思,讓獨立的推理及判斷令更多人清醒地看到自家直觀的政治取態的內在矛盾,視公眾意向為習慣、權威、傳統積習而成的愚昧。他本人則疏離公共生活,棄絕城邦的集體行動,既不向潛主的施政威權低頭,也不賣民主暴政的賬,令人想起後來梭羅主張的「公民抗命」和羅爾斯的「正義論」。但公民是否能將其自身的道義擺在法律之上?乃是霍布斯在十七世紀曾出盡全力為之辯護的題目, 也是直到如今一切保守派反對任何變革行為的理據。我們該怎麼看柏拉圖面臨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