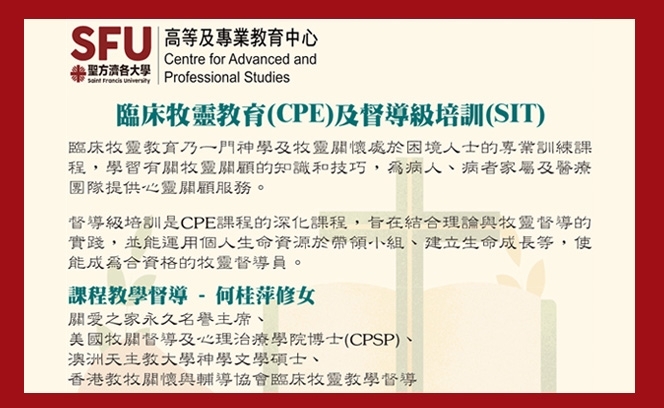【在人間】「老大哥」是怎麼煉成的?

對謊言深惡痛絕。他說,真正的謊言是人神共憤的,因為沒人會接受說謊的靈魂,沒人願意有不見得光的人藏在身邊。人生來既不願意欺騙別人,也不願被欺騙。說謊是一種邪惡,人們不會自願成為邪惡。但在《理想國》中,柏拉圖筆鋒一轉,謊言不但可諒解,還是好東西:邪惡是一種社會現象,誰都不能免俗,有時不得不說假話。但這「撒謊」只是修辭上的, 也不完全是謊言,因為它對人有用,有治療和預防功效。他認為,謊言是必須嚴格管理的「處方藥」,支配權必須給予醫生。統治者為國計民生,有理由用它來應付敵人和公民,其餘的人一概不准染指。一般人對統治者說謊,就像病人對醫生說謊,運動員不把身體的真情告訴教練,水手不把船隻的現況告訴舵手一樣,是有罪的。一般人最重要的自我克制是服從統治者;統治者最重要的克制是控制飲食等肉體上快樂的欲望。這高論令人想起中國文化在暴秦時代發明到如今仍發揚光大的「以吏為師」,孔子說「唯上智下愚而不移」……在上者的自大和專橫躍然紙上。柏拉圖愛把目的和手段區別,仿佛要實現偉大的目的,即使手段骯髒也可以理解。但在政治中,甚麼是手段?甚麼是目的?常給魚目混珠。若說謊言只是手段便可接受,別忘了用謊言得來的,也得用謊言去維持。都說一個謊言要用一百個謊言去掩飾,寧不會有信用破產的一日?若連目的也是謊言又如何?西諺有道,政客都是這麼一些高手,他們有本事哄騙許多人上了自家駕駛的船, 卻連這船會駛向何方,自家也不知。哪個政客敢說,他許諾的烏托邦不是謊言?人們都愛講初心,仿佛初心有善意,即使結果害人不淺也不必非議,但善意的謊言難道就不是謊言嗎?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柏拉圖未成年便熱中功名,儘管常碰得頭破血流,卻一有機緣便躍躍欲試。像後來的盧梭一樣,他屢替好些小國之君起草憲政文本。雅典的直接民主在伯利克里時代成為立國宗旨,在古代世界卻是異數,為周遭的王權政治包圍。即使在民主制如日中天時,富人和貴族仍不甘蟻民參政而蠢蠢欲動,宿敵斯巴達也一次又一次地扶植雅典的潛主來當自家的代理人。出身於世家大族的柏拉圖即使無貴族的傲慢,也不乏天將降大任於斯人的自許。而蘇格拉底卻一早就遠離政治,在柏拉圖早期對話錄中,蘇格拉底始終認為,自家被神諭認為最有智慧,是因為他自知在神面前,自家的智慧一文不值。他一再勸誡學生「認識你自己」, 「凡事莫過度」,即正視自己的局限和無知。但在《理想國》這篇中期對話錄中,蘇格拉底卻仿佛在人間築了座巴貝耳塔,讓自家立於其上呼風咤雲,不但以為自家在替天行道,且許諾給凡人一個最完美的國度。而這烏托邦到底是怎麼一個「好」法?我們在這二千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紀早已領教良多。柏拉圖筆下的蘇格拉底如何由一謙謙君子變得一朝得志語無倫次,可令人意會, 《1984》中的老大哥是怎麼煉成的?
哲學求真求善求美,別有天地非人間,一旦在俗世著地,也最易掉到最不乾不凈之境。智者變成奸雄,有時不一定因其立心不良或天生邪惡。活在短暫的人生,誰不想做出一點甚麼名垂青史?這可是最致命的誘惑。過分熾熱的功業心最易令人走火入魔。做成世紀特大災難的,常不是智者和英雄缺席,而是芸芸眾生的庸碌無知, 加上大人物虛火裡的偉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