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從「秩序感」想到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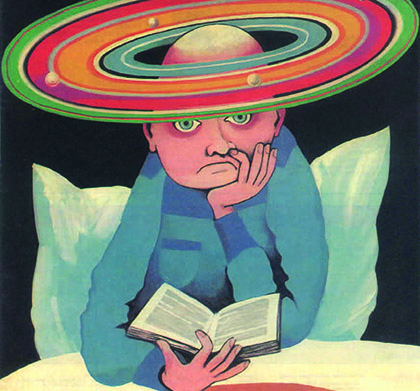
年輕學畫時,讀了不少如阿恩海姆的《藝術與視知覺》和貢布里希的《秩序感》之類的書。後來才知這類對人類視覺心理的探索,上世紀三十至六十年代, 格式塔學派(又名完型心理學)著力最深。這派學者擅長探求視象中的模式、形狀、形式背後人腦的運作原理,把本來玄之又玄的美感話題,放到人類要好好生存,就得給自家建立秩序感這最簡單及原始的需要來理解:美感可說是我們千萬年來生存經驗積累下來的副產品。我們認可「秩序就是美」,是因為先民在野外求生得「一眼關七」,特別喜歡排列有序的事物,久之,秩序感便化成視覺的愉悅感。但物象若全然符合秩序, 又會令視覺疲勞,於是「萬綠叢中一點紅」便令人覺得美不勝收。這些古今藝術家常玩弄的把戲原都有視覺秩序在幕後作祟……我記性差,當年讀的雖振聾發聵,如今都水過鴨背,只記得貢布里希說過:若無秩序感,我們便不能推算飛馳的車子何時逼近,連過馬路也隨時會給撞死。秩序感是如斯重要,讀不久前才過身的德裔美籍哲人沃格林五卷本的《秩序與歷史》,發覺他也從秩序感入手去理解人類文明進程。此書雖行文艱澀,細細把玩卻卓見處處,邊讀邊梳理自以為懂得的,常覺今是昨非。
《秩序與歷史》爬梳的是由蘇美、埃及再到以色列和古希臘,西方思維方式怎麼從原初開始,在各個層面上發展出各自不同的秩序意識, 又怎麼約化成各種文化符號,在古典世界中彼此分分合合,最後匯合為中世紀到近代的意識巨流。讀到西人說自家的痛癢,很自然便會和我輩熟悉的「中國傳統」兩相對照,便會想起我們中國古代的文物辭章中,先民尚在茹毛飲血時,就在不住積累秩序感以規範個體或集體的行為。古人愛把一些帶有根本性質的元概念以「一」稱之,說「道者,一立而萬物生」,認為這類原概念是「眾有之本,萬象之根,見用於神,藏用於人」。一見一藏,見用為法,藏用為道;法為人顯,道自天立。所謂道和法,都和秩序有關。令人想起柏拉圖說「存在是一」,「善就是一」。每個人或族群往往把多年生活經驗積存下來的秩序感視作顛撲不破的公理。歷史則常表現為不同個人或群體實現自家認定的秩序的爭鬥,且定然以「神意」或「天理」為意符,當作宇宙間的至理。
由是想起成了我們古代給兒童啟蒙的通識讀物《千字文》,其實就是古代國人秩序感的小百科。個中幾百個詞匯,可視作古代中國文化的意符大全。此文下筆伊始便說「天地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張。寒來暑往,秋收冬藏。」由天界說到地界,點出宇宙秩序後,即由神話轉入天人合一的歷史觀:「龍師火帝,鳥官人皇。始制文字,乃服衣裳。推位讓國,有虞陶唐。弔民伐罪,周發商湯。」再從歷史轉回現實,讓神界的秩序指導人間的秩序,力陳「皇天下」永垂不朽,草木人畜都得順應:「坐朝問道,垂拱平章。愛育黎首,臣伏戎羌。遐邇壹體,率賓歸王。鳴鳳在竹,白駒食場。化被草木,賴及萬方。」最後則以「謂語助者,焉哉乎也」來收尾,連該怎麼用言詞來傳情達意,即如何以約定俗成的意符,去為這包容一切的秩序感說事,都交待妥貼。宇宙,大自然,天、地、人三界給說成一體,活在這秩序之下,誰都要謹守規矩。中國人古來的秩序感,便是如此這般地給塑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