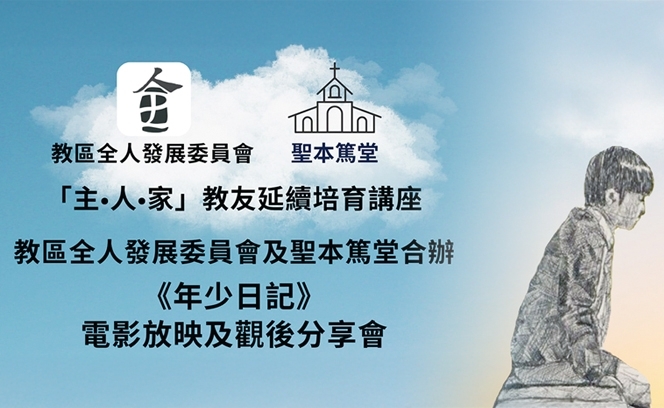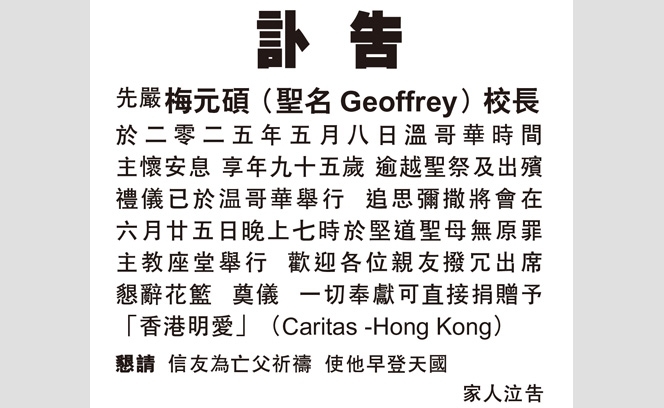【在人間】參與永恒

哲學書愛說「存在」是元概念,萬事萬物的概念都始於此而終於此。但「存在」關乎永恒, 若置入真實的人生,馬上顯得不著邊際。人活在世上,能直接經驗到的不是「存在」,而是「生存」。許多人要胼手胝足,一家大小才有存活機會;且無論帝王將相販夫走卒,誰都不過短短數十載,大限一到則灰飛煙滅。我們把存活的那段歷程稱為「人生」,無數如此這般的短暫人生匯合成了延綿不絕的洪流。它無形也無可界說,「抽刀斷水水更流」,誰都截不斷堵不住,也無一刻停滯,令人想起古希臘晦澀哲人克拉赫利特的名言:「人不能兩次出入同一條河」。孔子在河岸上概嘆「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宋儒說這是見「道體」之言。「道」即真理,「道體」即存在。孔子看到大河滔滔之水聯想到「時間之河」,以此象徵無始無終無限延展的存在。有說黑格爾的書充滿歷史感,孔子的概嘆不也極富這意味?
每個人都曾在這永恒之河出沒。之前和之後都有無數芸芸眾生在浮沉。所謂歷史和族群意識,與及內蘊的文明因子,都沉積其間,也塑造每位芸芸眾生的靈魂。每個個體即使多卑微,都參與了這永恒之河的造化。明乎此,說人類自有文化起便在追尋神聖事物,神聖事物是意識結構的基本原素,就易理解了。人都會死,若有人為這洪流增添了光采,其短暫的生命便多了一點意義,在參與永恒這意義上,可說戰勝了死亡。文天祥說「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說的便是這境界。而他的《正氣歌》也活畫了一位正統中國讀書人中的英雄豪傑的世界觀和存在感:「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 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現,一一垂丹青… …」「養氣」之說原於孟子:「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其為氣也,配義與道。」「氣」指精神性的正氣,宋代理學家張載以「氣」為宇宙本體,朱熹以「理」為世界本原,強調「氣」能化育萬物,在他們看來,「氣」是「理」與萬物的媒介。文天祥的老師歐陽守道(巽齋)是朱熹的再傳弟子,文氏本人和當時的許多士人一樣在理學浸潤甚深。這首五言古詩中關於正氣的鋪寫,可視作近代主宰了中國知識人精神面貌的宋明理學的正能量敍事。山東曲阜孔廟大成殿兩側有兩排房屋,稱為東西兩廡(附圖)。裡面供奉了一百多位歷代大儒和名臣的牌位,是二千多年來儒家道統公認的傑出人物。在這廡廊裡走一遭,你會更明白,古來正人君子嚮往的「流芳百世,位列廟堂」,是甚麼境界?文天祥的《正氣歌》又為何以「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的句子作結?
人可以活得像動物,也可以活得像天神。同是死,可重於泰山亦可輕於毫毛,世人的評論永不可能一致。同是對於生命的神聖感,不同人等可代入全然不同的具體方向,形成不同的信念, 成就了大千世界中的無數紛爭。宋明理學不過像無數西方曾出現過的種種「主義」一樣,把宇宙間的秩序比作人間的社會秩序,把人箝鑲在其間,很自然便會把動物化的生存趨向視作世俗的抉擇,精神層面的要求則視為向神界超拔。《聖經》說上主照自家的樣子造了人。中國文化沒有希伯來人的創世說和基督信仰的救恩說,「子不語怪力亂神」,《論語》談得最多的不是「神」而是「聖」,在聖賢身上寄托了人性最優秀的一面。研究任何文化都不可或缺的神聖感如何塑造了中國士人的靈魂,對於理解我們自己,是饒有意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