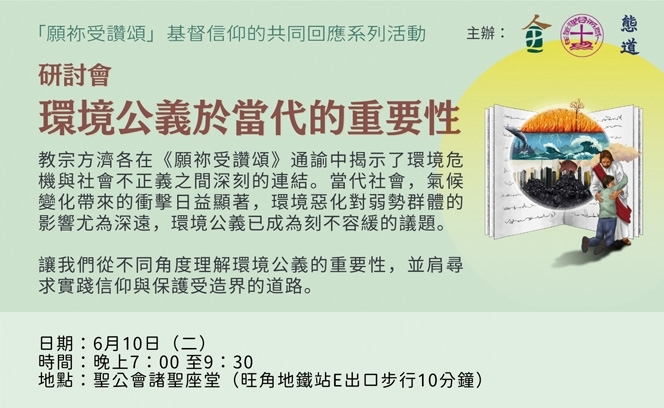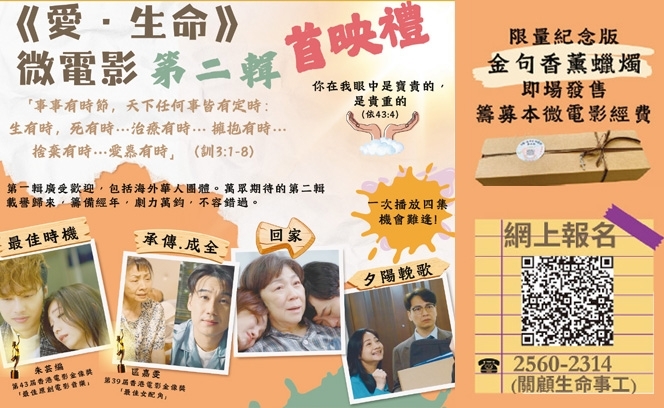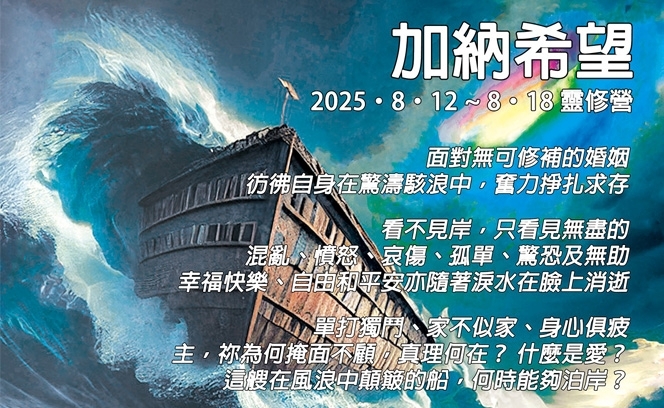【在人間】書寫

宋人筆記《宋稗類鈔》有段蘇軾的夫子自道:「某生平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踰此者」。說人生至樂無過於能把辭章未必能說清的心得順暢傳達,並非自持聰明,而是深知文章不易為。舞文弄墨者碼字如吹水,當然沒甚難度;而人若心存忠梗,便得直面沉苛的現實,下筆怎會輕鬆?昔人說人生至境是物我兩忘,即讓自家的生存與永恒的存在融為一體。生存是有限的存在,以一己有限的識見,任你學富五車,腦袋裡能動用的不過是前人積存下來表意符號,乍看浩翰無邊, 用起來不免蹇腳,洞見若超越前人,說清談何容易?如能把不吐不快的心事表達得淋漓盡致,便像三魂七魄出了竅,置身於與世界及與昔間聖賢渾然一體的境界。杜甫說「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說的是畫家筆下的山水仿佛有股天地混元之氣浮動,浸潤了屏障,仿如向冥冥中的主宰泣訴,連天地也為之動容,這境界豈止於畫道?自古有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人誰甘心朝生暮死?由是自古大塊文章總脫不了探索永恒,心繫天地。而人無論廁身任何文脈,總會在某個層面上觸碰到不可或缺的神聖感。芸芸眾生最愛問真理正義值幾錢一斤?但即使活得最卑微侷促,誰不努力給自家苦心經營出一塊半塊像個人樣的正直標貼?
蘇軾是詩詞和古文大家,可惜世人常只稱道其文才,忽視了他原是「文以載道」傳統的重要人物,對儒家經典見解獨到。近人接觸的儒學大抵不出宋明理學那套主張,史書大都以為理學的師祖是程朱,其實朱子之學在南宋後期才開始逐漸得勢,蘇軾和王安石才是北宋理學思潮草創時的大方家。王學曾作為官方顯學凡七十年,蘇軾的蜀學與之抗衡,在南宋盡領風騷時,閩學還未成氣候。周敦頤和二程在生時的顯赫地位是後人在理學成為官家標準意識形態後追加的。蘇軾說「孔子曰:言之不文, 行而不遠。又曰:辭,達而已矣。求物之妙, 如繫風捕影;能使事物瞭然於心者,蓋千萬人而不一遇也,而況能使瞭然於口與手者乎?是之謂辭達。」 「辭達」出自《論語.衛靈公》,孔子說文辭是為表達思想,後人便以為文章能說清道理便物盡其用,得魚即可忘荃。殊不知讀書人若不人云亦云,上窮碧落下黃泉,天門若偶而打開一扇縫,讓你一窺永恒堂奧,要把這驚鴻一瞥的心得寫下來,怎會容易得像斬瓜切菜?要用有限而具體的象徵去傳達涉及無限的意象,有時便得「言有盡而意無窮」,由是東坡才有「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隣,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的經驗之談。
寫作難,許多人為求佳句廢寢忘餐。傳說李賀的母親說「是兒必欲嘔出心乃已」,並非過論。蘇軾有位比他晚一輩的同鄉叫唐庚,稱「小東坡」,為詩為文最愛以蘇軾為榜樣,卻常為詩所苦,說自家悲吟累日,僅能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明日取讀,瑕疵百出,輒復悲吟累日,方敢示人,然終不能奇。他說「詩律傷嚴似寡恩言」,視文字如酷吏治獄,自家便仿如流刑犯,寫詩是活受罪。錢鐘書《宋詩選注》說他「在當時可能是最簡練、最緊湊的詩人,只是煉字鍊句常弄巧成拙。」人是最愛自設枷鎖的。昔人云「文字覷天巧」,為詩為文固然講才氣,但最大的才氣不在文墨,而在於對關乎永恒(即「道」)有多少心得。辛詞說「平生插架昌黎句,不似拾柴東野苦」,嘲笑的是孟郊視韓愈為神物,說「我願拾遺柴, 巢經於空虛」,辛詞高屋建瓴,高下立判。史家蘇辛並稱,稼軒與東坡是否心有靈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