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訓詁和訓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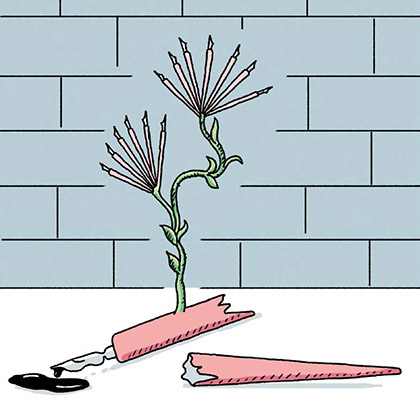
兒子告訴我,小時愛在我的書架找書看,有次翻出一本《訓詁學》,想:「怪不得給老爸教訓時我常無言以對,原來他懂『訓話學』。我長大了也要讀這書,好能教訓兒子。」如今想起這事,常忍不住笑。但回到現實卻笑不出來。蓋「訓詁」即「訓古」,窮究的是如何解讀古文。《論語》說「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認為讀書為的是自家長見識,為在人前炫耀而學便失卻意義。功利或虛榮是凡人難免的淺薄,對「為人而學」者其實不必太多指責;最恐怖的是世上常有人讀書只為武裝嘴巴,黨同伐異黑白顛倒。人把書讀到能令眾口「唵然無聲」境界,「訓詁」便等同「訓話」,不可謂不厲害。
書是買來讀的,拿來武裝書櫃雖不足法, 但附庸風雅總比焚琴煮鶴好。何況買回的書也不見得定然讀得完,誰也不敢說自家就沒有暴殄天物。見人引經據典捩橫折曲,其實也不必太生氣。若人人只說真話,這世道豈不早就成了天堂?還需甚麼救贖?常說謠言止於智者, 但世上智者何其稀罕?壞人靠著冰山,引來前呼後擁者眾,也合常理,耶穌不是在曾迎接過他榮進耶京的芸芸眾生的叫罵聲中被釘十架的嗎?二十世紀有幾位大哲都曾提供過這麼一個視野:人類在近代的自我折騰,皆可回溯到基督信仰草創時期的異端諾斯替主義(一譯「靈知派」)。異端乍看是某走火入魔者的發明, 後面總有嚴酷的現實背景和人群永不會汲取教訓的不智,自以為在替天行道者常愛秉持拜火教式的二元對立的思維習慣,死心不息地要在現世建立一個又一個「完美」世道,由是巴貝耳塔式的故事也一次又一次重演,先是以悲劇,後是以喜劇……筆者識淺,不敢強作解人,但若信頭頂有天,便知看似無理的陸離世事中,常隱含著某種至理。這至理也未必為我們完全陌生,在古代經典裡早有猜測和預感。有識者不必跟著潮流呼天搶地,何妨熱腸冷眼,好自為之?
手邊有套日本講談社的叢書(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二年中文版),叫《現代思想的冒險家們》,共三十一卷,每卷由一位日本學人寫一位西方現代哲人,共三十位,海德格爾、雅士倍、拉康、羅爾斯、榮格、阿倫特等都在其內。首卷由四位作者講了四位哲人:馬克思、尼采、佛洛伊德、胡塞爾,視他們為這三十位現世大哲的前驅,竊以為把這四人聯成一線,即使不能算是現代思想史的譜系,也代表了一個軌跡,許多人想法的改變,都和這軌跡有關。而現代思潮雖未必全都可上溯到胡塞爾「現象學」,但如果不讀他,從黑格爾到海德格爾就很費解。現代歷史很難迴避馬克思的書,要讀懂他便得讀懂黑格爾,還要讀懂康德,最好把叔本華和齊克果也串連起來,涉獵盧梭、伏爾泰。要更上層樓,得往上溯源讀中世紀的阿奎那、奧思定,再順流而上去讀塞內卡、西塞羅,還有亞里士多德、柏拉圖……這些人的書都曾被目為經典,個中片言隻語的確也曾被當作訓誨萬民的金句。若你讀這些書的目的不是為給人「訓話」時武裝嘴巴,而是像「訓詁」般查根問柢,便會發現書和書總是在對話,在作者之間穿梭便有如旁聽高人雅集, 可聽到他們在爭論和切磋。你也不必定要信服誰,對他們的分歧大可存而不論。他山之石, 可以攻錯,若對他們曾心繫過的東西有所認識,起碼令你對我們眼下面對著的是甚麼,容易心中有數。(書的故事·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