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間】水過鴨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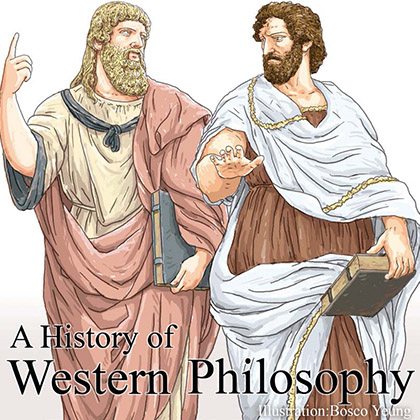
我家的書架擠著五套西方哲學史,有些早已翻得殘破, 但閒來重讀, 幾乎都水過鴨背,竟陌生得好像從未過目一樣,但對整套書的印象還算清晰。記得羅素那套是四十年前讀的,歷代大哲在他筆下仿如熟悉的同事和近鄰,個個如數家珍,其主張都爬梳得玲瓏剔透,讀來令人感到,哲學就在最尋常見慣的人生裡,和每個人對生命和世道的體察息息相關,那震撼感至今尚存。柯普斯登那套是在九十年代初讀的,為我是大開眼界:一向知道士林哲學本是中世紀經院哲學,博大精深。卻一直等閒不敢狎近,只停留在「望洋向若而嘆」段落。讀了該書,才知原來從這角度看世界,可如此開放,如此有說服力,卻如此平實,也破解了我對「理性」局限萌生已久的疑惑。之後再讀的兩套,一為門德爾班所著,特色是把哲學史分為幾個大範疇,即把以往哲人的探討整合為幾個大哉問,讓每位哲人都各歸其位,看看他們各自尋到的答案是否得當。我猜,若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九泉之下碰上作者,定有大把爭拗可令我們大開眼界。另一套的作者為梯爾,特點是觀點持平,不偏不倚。整部人類思想史在他筆下就像一灣清澈流水,讀來令人有若孔子坐看大河東去,在輕嘆「逝者如斯夫,不捨晝夜」的同時,自能領悟許多不能盡說的感悟。最近讀的那一套是勞特利奇出版社的十卷本大製作, 此書是集體執筆, 動用了一百三十位學者談由古到今的哲學思潮沿革,據說作者都是所談學問範疇的一時之選,近世學界的爭論都在書上有所反映。讀之如讀百科全書,迄今為止,方家們說過甚麼?後學該知道的,大都包含在內了。
我記性不好,睡前慣了挑燈夜讀,醒來卻常連昨晚讀過甚麼都記不起,有時忍不住問自己讀來幹嗎?但讀是難以抑制的興趣。古來不是有說,為學「只問真不真,不問用不用」嗎?記憶和忘卻其實是一對孿生兄弟,我們日積月累的訊息幾乎到爆炸程度, 不善於忘記,怎善於記憶?佛洛伊德或榮格總是一再提醒我們:所謂忘卻的東西,並非真的水過鴨背,而是化作無意識的片段和碎片,給壓縮在意識閥門以下,合成了一個潛藏在我們意識深處的無意識海洋。意識,即能記起能述說的,只是浮在無意識海洋上的小島。只要腦際出現一個關鍵詞,即觸動其中一個符碼,便有如在搜尋軟件裡按了一下鍵,底下必有許多思緒勾聯而出。讀後忘卻,有時未必不是好事。極可能在思緒深層,你日夕所讀的,早已潛而默化,化成更深沉的體會,只是你未必那麼容易找到話語來說清罷了。
書和書總是在對話,好的哲學史書,是把這些對話編織為一思緒之網,讓後學容易提綱挈領。平情而論,讀了這五套書的最大好處是,當我拿起一本談哲學的書,只要翻上幾頁,就能判斷是否值得讀下去。若值得,又該安插在人類思緒長河的哪個段落哪個範疇?讀過的書若都能歸邊,眾說紛紜便易理清,不會有若一筆糊塗賬。古人把藏書歸檔叫「插架」,韓愈(昌黎)說「鄴侯家多書,插架三萬軸」。他是古文大家,文起八代之衰,與他同代的孟郊(東野)說「我願拾遺柴,巢經於空虛」,辛詞卻說「平生插架昌黎句,不似拾柴東野苦」。人該見賢思齊,但對心儀者更宜心領神會,章句能記得固然好,讀後全都忘了也不必介懷。昔人說「得魚而忘荃」,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書的故事.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