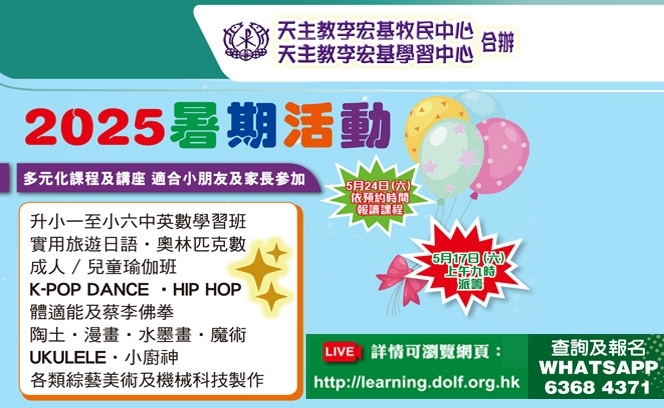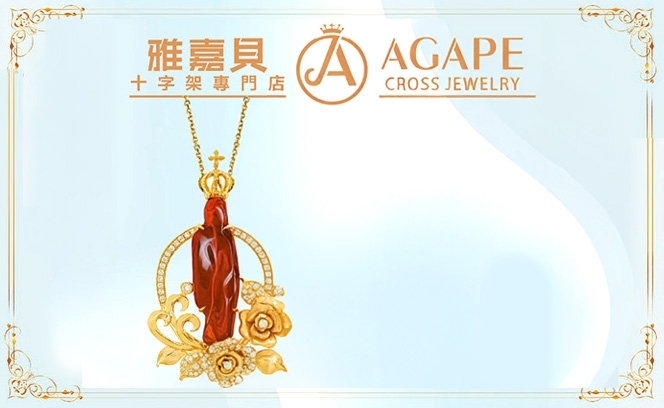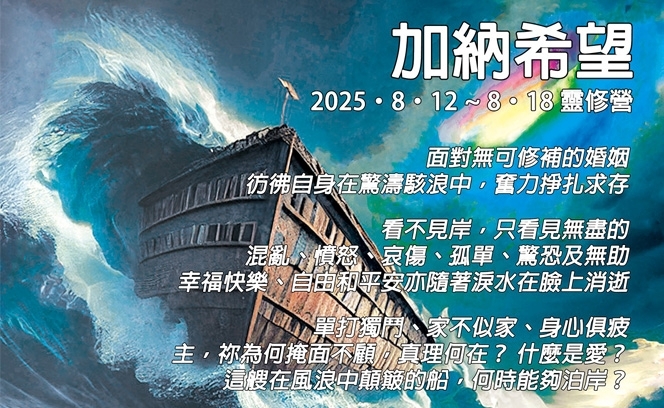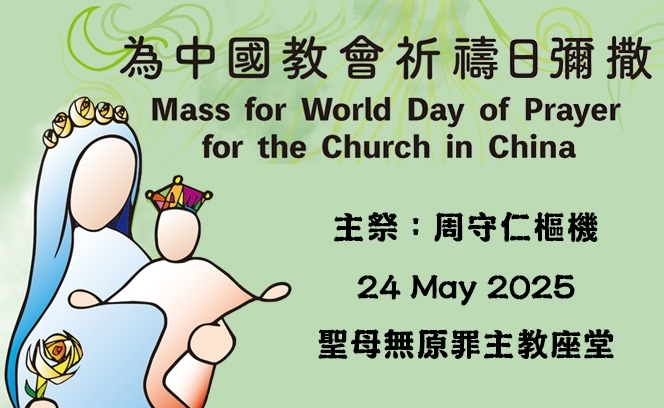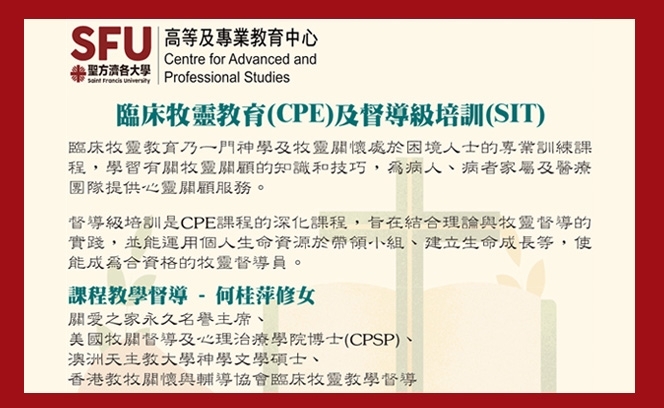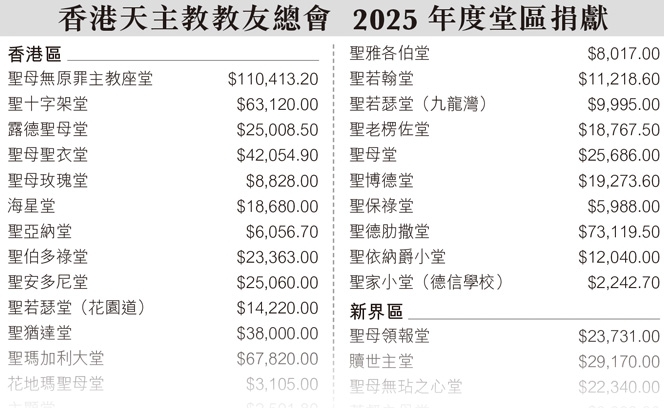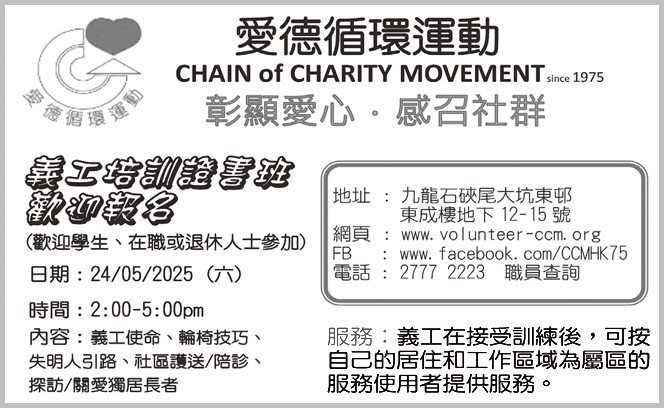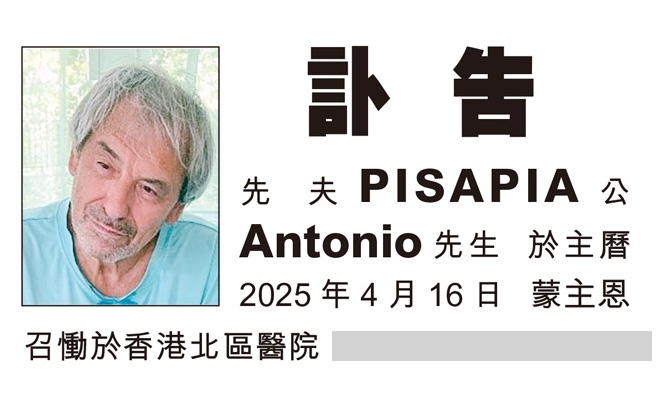【在人間】千古一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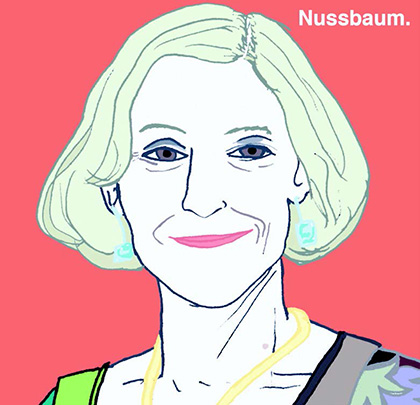
我們天天說話,卻甚少留意,語言是人類文明最重大的發明。重大到甚麼程度?坊間教哲學的書常說物質是第一性,意識是第二性,有物質才有意識…… 「意識」指人腦袋中的一切思維和判斷,但人能思維判斷全賴語言運作。若無語言,我們連關於我,關於世界,關於我願意或不願意…… 全都不知所謂,這第一性和第二性的分野更不知從何說起。不是說這區分全無意義,而是得認清:即使標榜為第一性的「物質」,一進入人的思維,和被貶低為第二性的「意識」一樣,都是供思維時好拿來作邏輯推演的表意符號。至於它表示的「客觀」世界是否真的那麼「客觀」,其實仍有待驗證。若未進入邏輯推敲程序之前,有待驗證的詞彙早就變得毋庸置疑。如此這般的語言魔術不絕於耳,寧不怵目驚心?
人靠語言來認知賴以生存的世界,不同的文化自有不同的自我解說系統。宋儒說「天不生仲尼,萬古如長夜」,可惜一出華文地域, 知孔子者不多;其實,人類若沒發明語言,那才真是「萬古如長夜」:芸芸眾生要用語言編織人生意義,哲人要用語言探索這世道是怎麼回事,語言一旦缺席,一切都子虛烏有,人類文明又從何說起?人生和有關世事的高頭講章,老子孔子稱之曰「道」,莊子有時亦稱之曰「理」。漢語起初一字一詞,後來發展出兩字一詞,便有宋儒大談「道理」,由是國人便「道」「理」不分。其實如韓愈說「由而是之為之道」,「道」者「路」也,指人生該行的路;王弼說「物無妄然,必有其理」,「理」指宇宙萬物必然之理;兩者不但有別,且是西方哲學爭論了二千多年的「本體與意義」的老話題,本是兩個不容混淆的思考範疇。西哲分而述之,不同範疇裡的是非曲直便易理清;中國文化無分彼此,許多本來不容混淆的觀念便易和稀泥,但由此也培養了直觀純真的詩性思維,亦造就了中國文化的風雅特色。而近代人愛談「理性」,不過是希望透過語言把握自己和客觀世界的底薀。但要弄清諸如「我是誰, 從哪來,到哪去」的大哉問,便得直面人的主體性和人與世界的關係。不但牽扯到本體和意義的分野,還出自人最原始的願望:想以人充滿局限的思維,去突破人思維的侷限,把握永恒。
有說近世是個「以頭倒立」的年代。「理性的覺醒」讓人激發起要把傳統信仰——拷問的雄心壯志,但懷疑論者若想不自陷虛無,便得找個錨點:世上還有甚麼是不可懷疑的? 「我思故我在」便應運而生:人總不能懷疑自家的存在吧?但「我」既是思維和觀察世界的主體,順理成章,「我」感到自家存在,世界才因之存在……人既把自家當作宇宙的中心, 卻又自知命如蚍蜉,何等矛盾?難怪古希臘悲劇總是充滿在命運面前人生何價的感嘆。讀當代女哲人納斯鮑姆(Nussbaum)的《善的脆弱性——古希臘悲劇與哲學中的運氣與倫理》一書,很難不佩服她在運氣與正義,情感與理性,戲劇與哲學,古代與現代之間,找到一條廢棄已久的通道,理解我們的文化自誕生起就得面對的難題。她是從「善」這詞語應被理解成為「幸福」還是「品格的善」開始探索的。我們也可像她一樣,直面人既自大又自卑, 「心有餘而力不足」的千古一嘆,透過詞語, 探索人性的奧秘嗎?
•本欄作者楊志強因事停止「在人間」專欄, 特此鳴謝作者多年來為本報撰稿。——編者